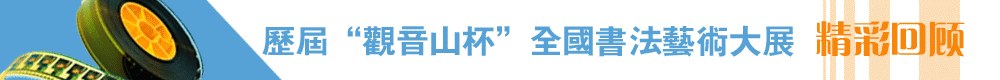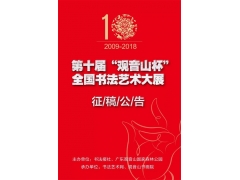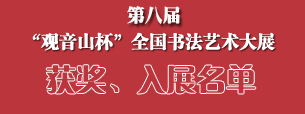记得是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光景,一日路过一家店铺,见店堂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草书四条屏,年少的我见了便极喜欢。当然那不是用来卖的,挂在那可能是源于习俗或是因为店老板的喜好。我们那儿乡俗家中有悬挂书画的传统,因为斯时地方经济不是很宽裕,故而只能挂一些古代的、当代的、有名的、无名的作品的印刷品,以此来体现一下地方文风或标榜主人的品位。于我来说,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慢慢地陶醉了,启蒙了。至于那幅四条屏,现在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位书家书写的了,有点象黄庭坚、祝忮山那一路风格。当时看不懂,就觉得很美,见之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以至于每天上学都要绕道去看上几眼,看呆了还经常迟到,继而在不懂草法的情况下便大胆开始了草书“创作”了。现在想来那时的举动是很幼稚可笑的,当然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书法研习中,一直以来有很多的想法,却没有很好地去整合,只是很零星地在记忆思维中散发着,我也常说“一个性情再好的人,也离不开理性的思考支撑和习惯的记录感悟。”想想也该用笔写下一点什么,将自己多年以来学习书法的心得与体会进行一番梳理了。
临摹是书法学习到创作的不二法门,所谓临摹的两大主要因素,也就是入帖与出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认清临摹的目的是什么——是继承古代优秀法帖的精髓,以至更好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如果说临帖是解决书写性及技法问题,那么读帖便是解决思维空间对书法深入理解的过程。学习书法非一朝一夕之事,有一个理解深入,渐修渐悟的过程,如果一定要说书法有什么捷径的话,那便是一个好的方法和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引导。儿时的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在一个很懵懂的情境,在父亲的引导下,对书法痴迷于心,家中的粉墙、地面都被我几乎写遍了。高中毕业后带着书法的梦想来到了部队,来到了苏州,在瓦翁恩师的指导下学习书法,渐渐对书法有了更深的领悟,常感悟先生所述书法本体的语言和书法以外的弦音。如刘熙载《艺概》中说到:“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先生常说:“字写工不难,当以写活。”并以此来要求我。在先生的悉心指点下进步显然,继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在黄惇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书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化的学习时期,无论是对技法的锤炼,还是对书法理念的形成,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黄瓜园之始,我不是太安分的去临帖,创作欲望特别强,很想有自己个性化的风格。黄老师一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说:“双阳,树上果实成熟的越早意味着什么?——坠落的越快。”同时还给我讲了一些古今的实例。黄老师的话,乃字字珠玑,给了我很深的启发,从而使我真正深入到传统的学习中去。时至今日黄老师的话我依然铭记在心。黄瓜园的时光是美好而又令人回味的,2001年底我经过四年南艺的学习后回到了如水的诗意般的苏州。
谈起苏州总让人产生几许依恋与遐想。谈到书法与苏州的渊源就深了,现存最早的文人墨迹陆机的《平复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孙过庭的《书谱》以及明四家的墨迹,对后来中国书坛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是历代名垂书史的吴门先贤。这样看来书法史如若离开了苏州还真不好延续的写下去了。应该说栖居于此甚为幸事。这里与金陵相比多了几许宁静,也使我逐渐静心来慢慢地理清了自己的心绪,给自己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以及自我的性情一个准确的定位。经过这些年砚边案头的耕耘苦度,一直也在思考着一些问题,有的感觉已经得到解决,有的还待进一步证实,已知的、未知的、有形的、无形的……都在我心绪脑海中交织着。
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宇宙是充满矛盾的,认识到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及相互间不断转换的关系。其中“混元”就是指天地万物混元生太极和阴阳,并且认为“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不可测量之谓神也。”阳动阴静、阳刚阴柔、阳虚阴实、阳舒阴敛、阳表阴里,并且还认为孤阳不生、孤阴不长,只有阴阳相互作用方能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书法自然也不例外。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王羲之也曾论过“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这说明从书法的本质中亦随处可见动静、刚柔、虚实、舒敛的表现,因此阴阳学说同样贯穿中国书法理论的始终。书法之博大精深,就在于根植于传统哲学之中,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到达一定层面应该是以老庄哲学思想去诠释生发的。老庄思想及《周易》应归结为“玄学”,当然“玄学”也是魏晋时期的主流学说。所以我们学习这一时期的书法,首先要就关注这一时期的人文精神及时代背景。如不了解这些,又如何去理解“二王”?认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认识它,把握它。“书肇于自然”是以汉字为载体加以个人情性的表现,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事物,经过那些古拙、自然墨迹线条和谐地联系起来,才能称之为书的艺术,是自然与人的天作之合。
近几年我主要是对魏晋以来“二王”体系书风进行全面的梳理学习,并对晋唐书风通过对其笔意、线质、章法的转换来表现,力求古为今用“大以小滋,小从大求”的学习创作理念。我们学习书法的手法可以是传统的,但我们对书法的理解与认识可以是全新的,我将此喻为“新瓷老酒”。 王铎与八大山人在继承“二王”,发展“二王”书风方面有着自我的理解与建树。象王铎能够把二王尺牍展大书写成条幅,在其章法、字势上增加了自我理解诠释,对当今书法创作是有贡献的,但是王铎在展大书写时为了增强作品的丰富性与单个字的饱满度,有意识地去增加字法缠绕,让附加线条与主线条同等存在,从某种角度讲,这样的书写很有气运流动性,也很有渲染力,与性情的挥洒很合拍,往往容易被欣赏者接受。但是,这样的方法违背了“简古、简淡、简雅”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也直接影响了观赏者对书法本质的主线条的审美。八大山人对“二王”书风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诠释魏晋“二王”书法,从八大山人的身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的发展便是最好的继承,他与王铎对“二王”的理解完全是两个方向。如果我们还按着王铎的思路去理解书法,很多东西是走不通的,走不远的,更谈不上走向深入了,那只可作为我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然而八大山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他那巨大的概括性和奇妙的抽象性,使他笔下的书法成为最简练的生命轨迹。
关于风格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书风的形成,作品风格成熟与否与他的成长过程及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从不否认对传统的偏爱,并没有过早的,很强烈的去追求所谓的风格,我想,一旦形成很强的风格,往往你只会去关注与你风格相关的东西,形成排它性,而不能做到兼容并收,融汇诸法。学习书法要学会抓住主脉络,要学会以一碑一帖去打通万法,在行草书创作中,《书谱》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是受益良多,可以断言,《书谱》是打通行草从临摹到创作的关键范本。我们对二王的学习不能只关注《兰亭》与《圣教》,不要以为写好它们就是学好二王了。要展开,二王是一棵大树,可取的面很多,如《万岁通天帖》、《大观帖》、《丧乱帖》等都是佳帖良篇,通过临习可以直接应用到创作中去。
言恭达老师说过,他们那个年代学书资料非常匮乏,借来一本《草字编》又没有复印机,只能通过双钩成帖。我们现在可以到书店随手翻到一本字帖,印刷水平越来越高,更方便的是网上下载,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敬畏传统,感恩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把字写好呢?
我也常对我的成人学生们说:“学习楷书并不是只为了写楷书,学习篆隶也不是为了写篆隶,最终还是一种融合。”所谓是“天下无物非草书”,可以断言,草书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书法艺术综合体现,是一种抽象的自然,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轮回。
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改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了。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弘一大师所言甚是!以此为结。
相关文章
- 格高莫过于八大山人2017-08-10
- 《汤文选谈艺录》选摘2017-08-08
- 2亿元兮甲盘的文字考2017-07-31
- 言论 | 传统文化断层导致美变异2017-07-26
- 书法无“韵”,只能落俗2017-07-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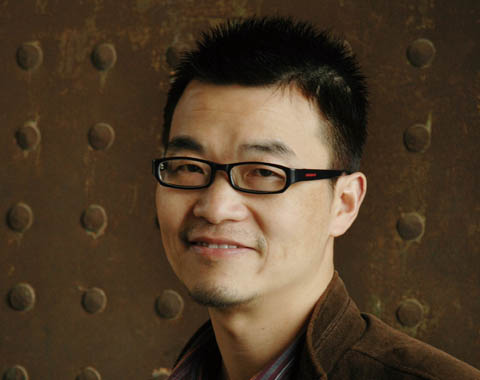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