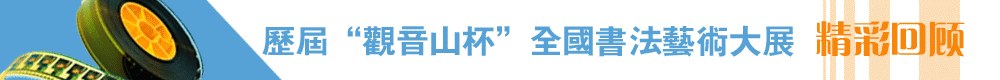宿墨多君变晶莹,最平凡处最关情。
交融境象开生面,淡远空明胜有声。
20世纪中国画最突出的成就在人物,水墨人物画以“现代浙派”为一大劲旅,而出身于“现代浙派”的吴山明又开创了不同师辈的“当代吴家样”,贯通了传统与现代,融会了人物与山水,形神并至,笔境兼夺。人物形象化入了氤氲的自然,神韵生动;笔墨像闪烁的黑水晶,单纯璀璨;意境像竟陵派的诗篇,淡远空明。其意象,境界和笔墨之美,显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在当代画坛上独树一帜。思考其成功之美和所致之由,显然是饶有兴味的,也会引出宝贵的启示。
发展意笔人物的两大问题
“当代吴家样”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水墨人物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断改变着突破前人的路径。在此同时,为进一步超越既往成就已出现多种取向。然而自古及今,水墨人物画的与时俱进始终离不开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怎样有效地扩展精神内涵,另一个是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笔墨与造型的矛盾。不找出统一笔墨与造型的新方式,既难以开拓新的意蕴与境界,也无法自立于各领风骚的古今画家之林。
自古以来,中国人物画便形成了两种体格,一为工笔,一为意笔(亦称写意)。在意笔人物兴起之前,占据画坛主流的是工笔重彩人物。当时,墨法尚未自觉,笔法主要是细笔的线描,可称“有笔无墨”。线描则服从于“应物象形”造型观,进而传达对象的精神气质,即所谓“以形写神”。意笔人物画兴起之后,占据画坛主流的已是写意山水与写意花鸟,此时,笔法墨法都得到了发展,既有了粗放笔法中各种形态的点线面,又有了墨法中浓淡干湿等变化,甚至一笔之内便见墨色过渡。不但讲求“水晕墨章”,而且刻意“笔精墨妙”。由于写意观念的深入人心,笔墨不仅要用以“状物”—描绘客观对象的形神,而且同时还要用来“写心”—表现画家的感情个性。相对人物画而言,写意的笔墨与精确的造型便成了不易两全的难题。
人们普遍感到,发挥写意精神,意笔人物大大难于意笔山水。明代徐沁指出:“能以笔墨开拓胸次而与造物争奇者,莫如山水、非若体貌他物,殚心毕智以求形似,规规于游方之内也。”他又说:“若夫造微入妙,形模为先,气韵精神,各极其变,如‘颊上三笔’,‘传神阿堵’,岂非酷求形似哉?”确如徐沁所见,画人物而不求形似,则对象个性全无,谈何传神;求肖似又势必影响笔墨的随心流淌,又怎么能表现写意精神,实现创作自由?以此之故,元明清数百年间,山水花鸟风行海内,名家辈出,山水更跃居各画种之上,以至有“画学十三科,山水打头”之说。而意笔人物发展迟缓,虽有卓荦不群之士,笔墨功深,造型精妙,但实属凤毛麟角。一般的意笔人物画家,为了笔墨写意的自由无碍,疏离了“应物象形”的古典造型观,略于形似,向山水花卉的宽泛图式靠拢,一意“以形写意”,加上选材的厚古薄今,创造的脱离生活,和画法的陈陈相因,致使意笔人物画的主流陷入了类型化的泥沼;丢失了“以形写神”的传统和持续发展的活力。
20世纪以降,志在振兴中国画的人物画家,为纠正明清人物画的流弊,引进了西方的写实主义,开宗立派,渐成主流。这一派大率以素描为造型基础,以笔墨(主要是勾勒皴染)为表现手段,使笔墨为严谨的造型服务,务求惟妙惟肖,由之公式化类型化被抛弃,人物个性得到突出,复兴了“以形写神”的传统,刷新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面貌,有效地表现了关系国运民生的时代心音。但由于矫枉过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求笔墨的形式美感和写意功能,在全面发挥笔墨传统的妙谛上若有不足。以“现代浙派”领军人物为代表的一批画家,继承了近现代水墨人物画取材立意的传统,筑基于坚实的素描速写功夫,掌握了高强的人物造型能力,又取法于传统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笔墨韵味与抒情功能,在前辈水墨人物画家勾勒皴染之外,广泛运用点、泼墨、没骨和破墨,于是变质实为灵动,成为现代水墨人物画中更加生动灵变的一支,在一定程度上为写实造型注入写意精神和笔墨美感,提高了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
开创“当代吴家样”之前,吴山明已是“现代浙派”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正当他寻找更适合于自己的审美方式与造型方式之际,新时期对古今传统的反思,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开放,为水墨人物画超越前辈提供了多种可能,题材选择从聚焦英雄人物扩展到芸芸众生,意蕴表达从思想感情的高亢昂扬的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艺术语言也从大同小异的水墨写实发展为多姿多彩,但因参照系的不同,约略表现为三种取向。一种以复古为更新,借径于意笔人物优秀遗产并不丰厚的古代文人画,尤着意于笔墨的写意,大多以休闲的“墨戏”,表现精神的超越,虽发展了非书法式线条的表现力,但往往描写古代人物,故在造型上重蹈公式化类型化者亦复不少。另一种以学西而求变,取法西方现代派,尤致力于造型的夸张奇变,求视觉的冲击,时空的幻化,虽在表现自我甚至开发潜意识上不无探索,亦刷新了视觉样式,但不少远离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笔墨奥义;第三种则努力深化晚近传统,坚持写实造型而力求突破,多能摆脱主题性绘画的文学性,谋求直观可视的绘画性,在描绘当代题材中,关注万家的忧乐,探讨水墨技法与西式制作手段的结合,虽丰富了画面肌理,但致力于传统笔墨挖潜并以新的方式实现人文关怀者,亦不多见。
吴山明基本上属于第三种取向的画家,由于师承“现代浙派”,在艺术思想上颇受潘天寿主张的陶融,深信中西绘画作为两大体系,相互间的吸收,不该削弱各自的特点,而应有助于拉开距离,使原有的传统更加丰满。对传统的理解,也不局限在技巧形式领域,而深入到文化精神和审美方式层面。在同样意义上他也颇受黄宾虹的影响。唯此之故,他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把深化艺术蕴涵和纯化绘画语言作为突破口,为此紧紧把握了两点。
一是反复走向生活,走向前辈画家未及充分关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发现耐人寻味的宝贵品质和文化精神。二是不断深入传统,深入传统的艺术精神、审美取向、语言方式、媒材技巧,洞察中国绘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髓。鉴于意笔人物画传统相对薄弱,他特别重视深入前辈“浙派”人物画家尚未深入的水墨画传统,特别是山水画传统,开发其尚可持续发展并引入意笔人物画的深藏潜力。
宿墨张力与写实造型
在对传统的深入开掘中,吴山明牢牢把握住笔墨相反相成的精义,和毛笔宣纸水墨特有的灵敏性与渗化性,努力在前人尚未充分施展的空间中,进行既纯化语言又强化视觉张力的离析与重组,经反复实践,形成了中锋笔踪和宿墨渗化相结合笔墨方式,似古而实新,奇妙而卓异。
传统的水墨人物画,讲求有笔有墨。而发墨离不开用笔,不通过一定的笔迹,墨的变化永远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为此中国画家向来在使笔中运墨,讲求一画落纸,是笔又是墨,充分发挥用笔踪迹的主导作用,高度重视“笔踪”。唐代张彦远就贬抑吹云之法,称其“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讲求笔踪,也就是讲究以笔法形态的千变万化和运笔来龙去脉的起承转合去状物抒情,但看重笔踪不等于忽略笔墨的相互生发,更不等于把墨韵变化死死控制在笔迹形态之内,无视笔墨生发中的随机性。没有这种随机性,便解放不了墨,容易失去天趣,“现代浙派”的绘画,比同时代的水墨人物画,笔踪无疑更丰富而有节奏,墨气也更灵活多变,但是墨韵的发挥仍局限于笔迹的框廓之内,少见墨法的机趣天然。
吴山明在纯化笔墨语言之初,画过白描人物,画过焦墨人物,也画过泼墨没骨人物,一次在藏区写生时偶以砚中宿墨作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精妙效果,引发了他对宿墨的苦心挖潜。宿墨指隔夜的墨,因静置已久,墨汁开始离析,部分烟粒有所脱胶,颗粒变大,色泽变暗,颜色近乎松烟,减少了光泽感,增加了覆盖力。作为一种墨法,宿墨最早在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里提及,以往画家偶尔亦用来丰富墨相,并没有物尽其用。能不能更多发挥宿墨的妙用,数百年来既无人想更无人做,一直到黄宾虹才在把宿墨列为“七墨”之一,在山水画中破天荒地开发宿墨的潜能。他运用宿墨中渣滓导致的行笔涩厚及水分渗出的意外之趣,凭借笔墨的交叉叠压,造成了既气韵流动又骨体坚凝的效果,亦苍亦润,浑厚华滋,化腐朽为神奇地开辟了山水画墨法的一个新天地。
“当代吴家样”的笔墨语言正是在黄宾虹宿墨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人物画的造型讲求确定性,宿墨的墨韵带有随机性,二者相互矛盾,在人物画中发挥宿墨,对于出身现代浙派的吴山明而言,必须解决两个化西为中的问题。一是变西式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观为中式讲求结构的造型观,二是变以笔墨服从于体面造型为主的手段为以线造型为主的手段。吴山明正是在不断钻研中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实现了笔踪与墨韵在水分冲击下的精妙生发,从而为意笔宿墨人物画的神明变化开拓了广阔空间。
吴家样的笔迹,充满变态又高度提炼,去掉了近现代水墨人物画皴染点厾,把点线面结合的笔法形迹,纯化为中锋的线,以短线为主,多成组使用,从整体着眼,不胶着于质感,不拘泥于次要细节,把握住最关键的部位。笔迹以碑味的凝重融入帖味的流畅,讲藏头护尾,一波三折,状如春蚓秋蛇,又多笔断意连。因使用长锋羊毫,蓄水多川流泻缓,落纸之后,既形成了沉厚有力的笔痕,又出现了笔痕框廓外的墨韵渗化,渗出了结构的凹凸转折,渗出了厚度,也渗出了韵味,起到扩张线条、延展笔痕而塑造形体的作用。笔痕框廓内外因宿墨脱胶程度及水分的渗润之异,更出现了或结或化的不同,其凝结处有干笔的骨力,但干而能润,其化散处有湿笔的缥缈,但虚中有实。这种笔墨语言极其单纯又变化自然,既意在笔先,又有一定自动性,既讲求传统的笔情墨趣,又不乏随机偶成的新异肌理,既得心应手,又天趣盎然,大略在有控制又不完全控制之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之美,实现了高难度的写意笔墨与高难度的写实造型的统一。吸取了西方写实人物画法的造型精微,但出之于有骨有肉,有气有血,有生命有个性的笔墨,强化了中国画笔墨状物写心的表现力。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的是一超越前人与古为新的创造。
山水意识与传神和构境
吴山明还十分重视开掘传统山水画诉诸观者的审美方式,特别是平淡有味地升华精神境界的造境方式。在中国传统美学的陶融下,平中求奇淡而有味的作品,向来被视为中国画的高品位,遗憾的是在古代山水花鸟画中时或有之,人物画殊为少见。近百年来,因社会变革的激荡风雷,振兴中华的庄严使命,有责任感的水墨人物画家,率多投入了火热的斗争选取重大题材,描写新的人物,表现新的思想。“现代浙派”的第一代画家,更能通过表现富于新意的生活情趣小中见大地讴歌新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但取自西方的写实观念与写实方法,一方面成为画家以文载道的利器,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对传统审美方式的发挥。进入新时期之后,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水墨人物画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也有一些作品太重自我表现,对内心情感的表现太个人化,甚至热衷于表现苦闷、迷惘,挣扎和狂躁的情绪,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简单袭用,消化不良。二是囿于画室生活天地狭小,源泉枯竭。三是不大注意以提升作品的精神境界陶冶观者,丢失传统,有变无承。
传统写意山水画亦不以境之奇怪为高,而以平中求奇为胜,追求在平常的景色中画出自然、历史和生命的统一。其实任何高明的传统艺术,都不是情绪的发泄,直白的叙说,而是通过涵养性情,净化心灵,使真情实感升华为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早已指出,“中国画所表现的审美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积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为了在人物画中引入这一精义,他走出画室,贴近生活,不断橐笔远行,下滇南,上天山,进藏区,入延边,去内蒙古,赴绍兴,在与最平凡最普通的各族老少妇孺的接触中,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悟解他们的内心精神,在这些宁静、单纯、质朴、有追求、富活力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他们生活态度的淡泊而积极,平凡而不平庸,他深深感受到这种世代默默支撑民族大厦的不朽精神竟是与静穆崇高的大地山河以及生生不息的历史同在的。这种直接来自原生态生活的深切体验,成为他创作淡而有味作品的源头活水。
如上所述,当不少画家如饥似渴的向西方寻找创新良药之时,吴山明却从生活感悟出发潜入传统特别是山水画传统,参悟其历韧不磨的文化精神,领略其升华精神的审美方式。他深感,传统山水画每从整体上观照世界,虽讲情景交融的意境,但殊少太具体的情与太具体的景,较多的一种理想环境与理想审美感情的交融,因此才具有一种静尘器,合天人,通古今的悠远之感,才把可记的景象提升为可钦的精神境界。正是这样的认识,造成了他的人物画创作总是在品味生活中发现,在回味生活中升华,在拉开距离中表现美,形成了“当代吴家样”涵泳生活的诗意与余味。吴山明的水墨人物画,尽管有的只画人物,有的略微点景,但他善于把黄宾虹使用的浓宿墨转化为淡宿墨,尤善于精心显现人物环境的光风霁雪云流日影,巧妙地实现了“粉碎虚空”,使“空中有画,着处无痕”,把人物与环境在相互渗化中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不仅描写了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把自己回味无穷的审美感情投射到天人合一的宁静含蓄光明悠远的境界中去。从而使自古以来以传神为依归的水墨人物画,成为以传神为基础以造境为主导的新面目,尽管不能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充分的实现了这一点,但就丰富人物画的艺术表现的途径而言,应该说,这是吴山明的一个创造。
吴山明的“当代吴家样”仍在发展,况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种艺术的长处发挥至极,其局限性也便显现的更为清楚。有的批评家希望吴山明多画些洋溢奋发之情的直接参与现实的作品,眼光至为锐敏,对于从中国人物画创作全局上把握导向也甚为有益,然而这恐非已有明确艺术取向的“当代吴家样”所能胜任。我倒觉得,吴山明倘能在精勤不懈的艺术生涯中,进一步强化创作意识,在保存其从原生态生活中提纯至味的条件下,与习作更多拉开距离,同时把塑造地方历史文化名人形象的意笔夸张手段用于描绘当代现实人物,这可能是他有条件付诸努力的,也将会使吴山明的艺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体素照神
“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庄子·刻意》)。
以素求真,古味至纯。山明作画不尚雕琢矫饰之工,惟以天真脱俗之心,于笔墨游戏中陶冶提炼,其画意自然落尽一切杂质,而现其皎洁纯素之体。以素为体,此乃中国人物画之根本所在。山明之“素”,在其早期创作中,于质朴简约中透露出鲜活的生命气息,而近年来,则表现为日渐洗练的笔墨所求达的体格之雅正、气格之清明。
山明作画,尝于笔势纵横间拓出自然形貌,于水晕墨彰中照出人物风神。近视之但见笔墨漶漫,退后三尺,少女、新妇、骄子、老汉、苦行者、牧羊人则一一跃然纸上。“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画者以澄澈虚灵之心观物,物自现其真形,心物两相辉映之间,人物之风神自在其间矣。
相关文章
- 张红春|西行日记2017-10-27
- 弘一法师给日本妻子的信2017-07-21
- 历史上的“中国美术学院”2017-07-13
- 吴镇烽《国宝百年失落 兮盘今朝重现——析论国宝兮甲盘》2017-07-11
- 魏晋风流岂无“凭”:文物艺术中的“曲凭几”2017-06-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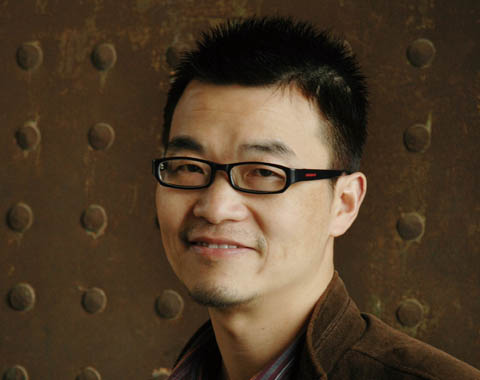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