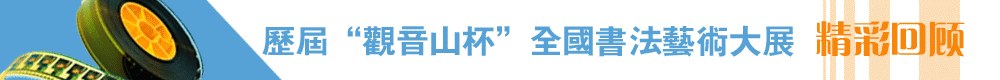笔法琐谈之12:无法
四川新都宝光寺,有清人何元普撰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我没有见过此联原作,其中“世外人”又有“世间人”、“方外人”的说法,不知孰是。“非法法也”、“不了了之”的观念,却影响不小。《金刚经》说:“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法种种,乃是度人之筏,倘若已经了悟,自然要舍舟登岸。
前几年, 孙晓云先生《书法有法》出版畅销,我认为,近年的“帖学热”,与之有深刻关系。帖学的复兴,也正是重新发现了笔法,并皈依笔法的结果。但也有人说,什么“法”,应该说“书法无法”。
然而,安知有法才能无法,无法正是有法乎?
禅宗是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一落言诠,便是下乘,然而其经籍又浩如烟海。这看似矛盾,却又不得不尔。没有形式,内容是无所凭依的。就书法而言,初期书论,鲜及执使转用的细节,大概宋以后,书论越来越形而下之。形而下之的结果是,说得越来越具体,然而书法却并没有越来越进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笔法,还是要谈。
一艺升沉,自有因缘。书法的盛衰,也自有气数。
铭石之书,大盛于东汉,再盛于北魏,到唐代与文人书、写经书相互浸染而合流,可谓大普及了,也可谓走到尽头了。颜柳之后,铭石书几乎没有什么成绩。
文人书的传承,起初只是口传手授,盛唐之前的大家,差不多可以由笔法传承串起来,亲戚、师生的关系,一环扣一环。也大约在初唐,二王书迹聚于内府,而复制品流入民间,特别是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这样的石刻,会被较多人所见,而《兰亭序》在士大夫间,也广为摹习。到了晚唐五代,已经有汇帖出现了。宋代《淳化阁帖》及其裔嗣,更是化身千亿,散布人间。这样的大普及,肯定促进了社会书写水平的提高。然而,物极必反,法帖也逐渐导致了“院体”,欧、颜、柳所书碑拓本,再加上后来的赵,称为楷书四大家,也形成了某种封闭和限制。元明后的大家,即使他们有机会看到历代墨迹,也差不多都在汇帖和唐碑的牢笼之下,更何况一般人?往往,一种艺术的最高境界,形成于初创时期。书法也不例外。真、行、草书,肇始于汉代,而造极于魏晋,再盛于唐,以后就难于产生划时代的大师。大概在唐季,进一步到宋代,书法普及了,笔法传承的链条,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个别有师承者,当然还能克绍前辈箕裘,维持笔法延续,而大部分人,不得不以碑帖为师、以塾师为师,或者“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了。而宋代的意识,也好像师古的风气不浓,所以,北宋大家之后,尽管宋代文人多,而书家却不多。南宋陆游、朱熹都能排得上座次,其技术水平,显然是不及北宋,更远不及唐人的,更别说东汉魏晋了。宋代一般学书者,很多人取法苏、米,也是目光狭隘的体现。元代赵子昂、鲜于枢显然在技术上有明显的进步,进步的根源,却正是学古。明代的吴门四家,可视为赵子昂的余续。而晚明书家群的出现,则差不多再现了北宋时的辉煌。晚明书法的中兴,与世风固有联系,也与厅堂立轴大幅的形制,以及新工具新材料的使用不无关系,王铎差不多做了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到清代,时移世易,书风又为之一变。
清代碑派,固然有历史的偶然因素,然而也确实存在康有为所说的“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的因素。关键是后来者必受限于先进者。即使尊碑,也无法绕开南北朝以降的一切。像龚自珍说的“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前辈碑派书家,往往教育后辈时说,唐以后不可学,但无论其本人还是后辈,不可能睁眼不看唐以下书法,也不可能不受唐以后人的影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本朝有四家,皆集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州也;集隶书之成,邓完白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学之成,张廉卿也。”其中,伊秉绶、刘墉、张裕钊,如果以书法史的眼光看,恐怕还都只是名家,当不起集大成的称号,晚清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等,与之颉颃。邓石如用隶法写篆,可谓篆书的中兴之主,隶书也自不差,而行草则几无成就。上述碑派书家群,以书法史的眼光看,顶多可以比翼吴门书家群,于赵、董尚逊一筹,无论苏、黄、米、蔡矣。总体而论,碑学的眼光局限于石刻,误“中锋”为一切法,在“中锋”这个无等等咒的基础上,结合羊毫笔、生宣纸,硬是创立了一套技法体系。这一体系,说是误会也行,说是创新也行。其结果是,擅大字而不擅小字,主运肘而不主转指,变化万千的笔法,变得相对单调了。孙晓云称之为“无法”,虽不好听,却也是实情。当然,尺八大屏,字大于掌,必求气势,暂缓精微时,其法并非无用,这也是实情。
实际上,清季碑派大家,并非不知帖派之妙。何绍基、赵之谦皆从颜起家,能写一手颜体行书。沈曾植本来就不轩轾碑帖,而是采用兼融并包的态度。连否定转指的康有为自己,晚年也曾经说过,如果再写一本书,就会转而提倡帖学了。这让人想到金庸《鹿鼎记》中陈近南、韦小宝关于“反清复明”的话。聪明人说话,往往带点忽悠,对芸芸众生,采取的是灌输思想的态度。然而碑学大倡的结果是,行草书全线沦陷,所以到晚清民国间,也就是在《广艺舟双楫》问世之后,纯正的所谓碑派,也已经走到尽头,转向“碑帖兼融”了。碑学之兴,似乎并没有解决帖学的问题,也不可能创立一套新的书法体系,与帖学分庭抗礼。而相反,不知帖,也就不知碑。因为无论如何,不管什么石刻文字,总是来于书丹原迹的;而碑派书法家也是通过毛笔直接写在纸上,而不是直接以刻石面世的。所以,当对石刻书迹研究时,面对菁芜杂存的金石书迹,写手与刻手的问题,就成为关注的对象。沙孟海、启功对写手、刻手的关注,与其说是个人的学术兴趣,不如说是书法史发展自然提出的问题。启功是倡导“透过刀锋看笔锋”的。沙孟海的一段话,更为著名。其《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云:“说句干脆的话,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序》也几乎变成《爨宝子》。”这话是说得有点过于干脆了,然而所谓矫枉过正,也无不可。秦汉简牍书的大量出土,是近百年的事情,前代人惑于石刻拓本,也情有可原。而直到现在,石刻是否传达书丹原貌,还是争论的问题。偏执于碑的人,往往认为不论何种石刻,均准确传达了书丹原貌;偏执于帖的人,认为圭角尽露的石刻书迹,皆是刀刻的结果。实际上,两者都未能执中而作持平之论。铭石之书,向有复古、庄重、矜持的意识,而其书迹经过刀刻,也不免有所修饰;进一步,书丹者受铭石效果的暗示,也有意地用笔去表现刀的痕迹。像《令狐天恩墓表》那样过于刻意模仿刀迹者,当然也是少数;然而,像唐代颜、柳之书的捺角,应当是对石刻文字有意靠近,并经刻手修饰后的结果。知道刀与笔的关系,才能够认识手中之笔,才能够发挥笔的功能,这就不仅是观念、流派的问题,而且也是技法的问题。近世仍有抱定《龙门二十品》之书家,朝勤夕惕,废纸以车,然而不究墨迹,终与笔法隔膜,书迹安排费功,有骨无筋,不能活脱,良可太息也。
综而言之,且不论古文字时期,则石刻书法的鼎盛,在东汉、北魏,之后乏善可陈;墨迹则两汉魏晋为极盛,初唐盛唐为再盛,北宋为后劲,晚明为余波。清代碑派,则如黄花梨的鬼脸,来于不得已的机遇,却有异样别致之美,说是奇葩,也无不可。石刻文字之佳者,为文人书家书丹,与帖是一身两像;而其不佳者,则石匠陶工不识字人雕凿,本来就是生毛桃,顶多有些趣味而已。简牍、写经、写本之类,精芜并存,上品不亚于经典法书,次品亦只可覆醅补壁而已。然而不佳之石刻、墨本,因时代悬隔,风雨所蚀,水火所侵,或竟生古意,偶一参酌,亦无不可;过去泥鳅、南瓜之类,不上酒席,如今也上了,但以为此为无上佳品,将废粱肉而进糠麸,则得非自弃欺人乎。诚如是,则笔法云者,仍只是一法,即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笔法,上溯则有汉碑简帛,下探则有历代剧迹,至于碑耶帖耶,经典耶民间耶,差不多就是伪命题。而二王笔法,也不过是书写得势得力,执使转用合乎生理、达其情性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笔法无法,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无法,才是一种解放。陆时雍《诗境总论》云:“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此之谓乎?
只有通过真正地掌握法,本领成为本能,才能达到无法,达到“水流自行,云生自起”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享受自由,纵任不拘,也便会产生绚烂的风格。即两宋以降,风格独特者,代不乏人,而细玩其起承转合,仍止是一法,并无神秘,大道至简,大道甚夷,并非欺人之谈也。
若林逋之书,清癯如不胜衣,而点画并非轻轻画过;康里子山之书,简率颓唐,而环转周密,并无缺失;杨维桢刚狠果决,如一团铁丝,而笔路清晰,并不见故弄圭角;倪瓒之书,画意灿然,而点画绵劲,筋骨血肉具备;金农之书,古灵诡谲,而点画应规入矩,何曾任意涂抹?历代畸士异人,面目迥不与人同者,笔笔有法,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为法缚,是为无法。譬若人之面目肤色毛发,或各不相同,而其生理,则何有大不同哉?
胸怀中庸正直,不失赤子之心,反能特立独行;法度不待思索,一任天真烂熳,乃能自成一家。有法无法,言尽于此矣。
相关文章
- 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2014-08-08
-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书法文化世界化2014-08-08
- [唐]欧阳询·三十六法2014-08-01
- [唐]欧阳询·用笔论2014-08-01
- [唐]欧阳询·传授诀2014-08-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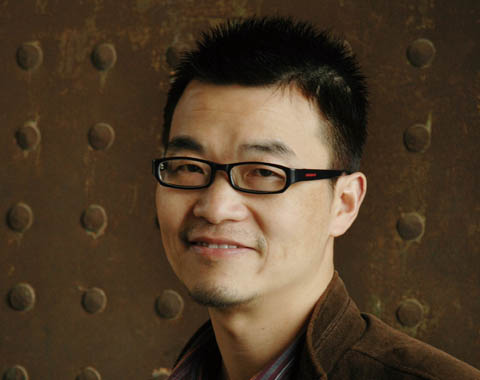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