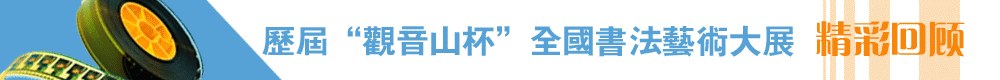笔法琐谈之11:气韵
王僧虔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张怀瓘曰:“深识书者,唯见神采。”然而究竟什么是神采,却很难一句话说清。如果酷嗜西人治学方法,会给神采下定义,并论列实现的途径。这其实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下力不讨好的事。好像启功说过,甜之一味,只要一尝,立刻就知道了,但要说清楚什么是甜,那就恐怕写一本书也未必奏效。
文艺之道,终究靠自证自悟,然而又不能不说。强以言之,则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人。有神采的人才能写出有神采的字。其二,是技,有技术的人才能写出有神采的字。而人与技,在神采这个层次上,是不可分割的。
人之一生一世,异于禽兽者几希。生老病死,转舜即逝。即便成为伟人,管领江山,与成为凡人,打柴牧羊,差别其实并不大。所以,成不成书法家,更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一生虽短,而差不多所有人却不愿苟活,总希望活出点意思来。这意思,如果撇开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回到人本身,则气质、风度就很重要了。魏晋人生于离乱之中,每感生命无常,就从本身出发,追求不朽,因而其文学艺术,格外散发出生命的光芒。而其气度,反映于书法,则后人拈出一个“韵”字概之。气韵,由是成为书家的理想。
蔡襄云:
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这样的话,值得一读再读,每读道一声好,个中意思,尽于此,多说都是赘语,正因其“不可以言语求觅也”。据说俞平伯先生上宋词赏析课,常常是读一遍,之后说:好,真好!个中意思,也尽于此。
黄庭坚云:
两晋士大夫类能书,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想可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谢赫《古画品录》论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根本,可谓真知灼见,千秋不移。中国文艺,讲究知人论世,如苏轼云:“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从大的方面说,人的品德也是要论的,个别情况下,不因人废艺,那只是一种宽宥而已。也许中国人对伦理是有点近于偏执地重视,然而,如果人物不美,艺术还有什么值得珍惜呢?即不论品行,至少,风度是一定要论的,因而书法还是以文人为正宗。这并不是说非文人德行有亏,而是所谓文,正是理想化的修饰,人之所祈向也。
也许这又牵涉到碑帖之争、经典书法与所谓民间书法之争。白蕉说过一段相当公允的话。其《书法十讲》云:
我认为碑版尽可多学,而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碑沉着、端厚而重点划;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萧散,乃见神采。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我们决不能因为有碑学和帖学的派别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笔抹杀。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碑中当然有文人、书家的书迹,积学所至,自然精彩。而不识字的石工、陶匠,终究风度欠缺,况于书法未曾用心,除了有些生猛粗犷之气外,还有多少可贵之处呢?白蕉以生毛桃喻之,听起来有点刻薄,实则恰如其分。今有作书者,务为倡导此类,差不多以为只有这样的字迹才艺术,而历代文士大夫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其奇嗜奇于包、康,真可令人发笑。然而此类倡导者,自己却身居要津,吃着供奉厚禄,享受万众谟拜,欣纳十分供养,怎么不去引车卖浆,彻底地进行书法革命呢?人无信则不立,口中一种说辞,而不能践而行之者,诈也。如果说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法也担当“成教化、助人伦”的使命,可能言之太过,也太实用主义了。但是,一艺之成,终究要有助于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否则,不但不可贵,简直就有点可恶了。
当然,有韵之书,必出于有韵之人;而有韵之人,不一定必写出有韵之书。赵之谦《章安杂说》云:“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真,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这是极而言之,以期警醒愚蒙的话。三岁稚子,当然能见天真,如果能写字,其字中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成年人也许是断不可及的;然而三岁稚子不怎么会写字,更为重要的是,三岁稚子一定会长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混沌凿七窍而亡,然则有七窍之人,谁愿意复归混沌状态呢?积学大儒,代不乏人,以书知名者,却也寥寥,这原因并不是因为学问掩了书法之名,而是其书迹本来就说不上好。虽然积学大儒的字,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书卷之气,会透露出一些别样的魅力,但书法终究是专门之技,也需要“别才”的,少了书法的才华,少了书法的功力,积学大儒也照样写不好字,这没有办法。司马迁的文才,可能登峰造极,但未必就能诗;杜甫的诗才,可能无与伦比,但未必就擅文,各有才情、各有造就,这是无庸赘言的。
由此看来,书法要有韵,不但关乎人的风度,技术也是必须的。有技术才有自由、才有流露、才有张扬。而掌握技术的过程是做作的、刻意的。只有经过刻意、做作,才有可能达到彼岸。学古过程,读其文辞,揣其笔法,日积月累,渐近古人,不唯是积累技术,也是积累趣味,时日既久,芝兰俱香,人的修炼与字的修炼,才能合而为一,以至于意在笔先,下笔有由,充分自信,任意挥洒。朱和羹《临池心解》云:
意在笔先,实非易事。穷微测奥,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缩攒捉,细心体认,笔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谓意在笔先也。
体察法帖之奇,通乎仰观俯察,自然、社会、人心、人生,事殊而理相同。顶天立地之刚,风流倜傥之奇,出世超脱之逸,百转千回之能,不可言宣之妙,一一俱在法书之中可以印证。比如临王羲之,何尝不嗟叹其字法之奇,匪夷所思,模而拟之,才会启智发蒙,出离愚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
新理异态,古人所贵。逸少曰:“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
道理是这样的道理,然而真做到“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却绝非易事。有不少初学书者会问,临习古人临到什么时间就可以了,或者说什么时间就可以自成一家,不再学习古人了,真是难以作答。真知书者,才会知道临习乃终身之事,与古为徒,犹日与高人逸士盘桓,必有所进,三日睽违,俗气横生于胸矣,终日闭门造车,师心自用,恣意挥洒,必日俗一日,安有气韵可言哉?有所谓好书者,颇负才华,初能挥毫,便不置古今书家于眼角,胡涂乱抹,自鸣得意,而群从欢呼,名家鼓吹,飘飘然不知有羲献旭素矣。然则其人其书,能言气韵乎?刘熙载《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需知学有科目,才有领域,至于志气,尤其位高财富名彰者未必定胜位卑贫寒而无名者,然而人之志趣气度,终亦在其书中矣。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刘熙载《书概》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又云:“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我辈学书,当以浩然之气为念,以士气为务,以此立身处世,方不愧先贤创为书法一艺耳。以此为念学书,才能克绍箕裘,以期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达到技术与性灵的统一。
若夫人而不俗,于技术能不假思索,则气韵自生。王僧虔《笔意赞》云:“心忘于笔,手记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书谱》云:“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忘乎所以,方能人书不二。至于碑版题署,或公然作书,往往重在骨气,不免有意为之,无论如何,还有有点欲人称工之意。而著述草稿,尺牍札记,实最能契于机趣,一派神行。王澍《论书剩语》云:
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料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
书如其人,则稿书最如其人;书有神采,则稿书最具神采。
絮烦如是,终说不出“祖师西来意”,不可说也。何如径看古人稿书耶?
相关文章
- 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2014-08-08
-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书法文化世界化2014-08-08
- [唐]欧阳询·三十六法2014-08-01
- [唐]欧阳询·用笔论2014-08-01
- [唐]欧阳询·传授诀2014-08-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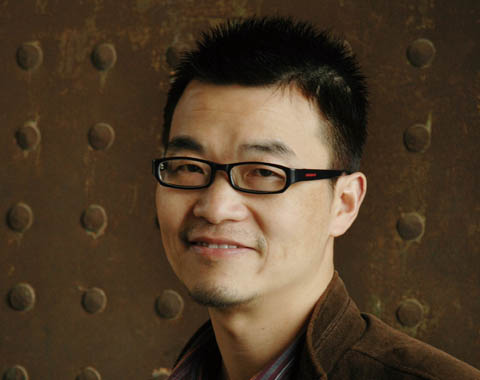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