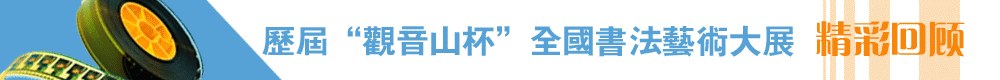父亲沈邦武与邓少峰先生的交往
2013-10-18 09:4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父亲沈邦武与邓少峰先生的交往
■沈必晟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父亲沈邦武就一直跟随我省金石书画大家邓少峰先生学艺,直至邓老1986年去世,从旁伺砚近30年。邓老离开我们又已经20多年了,时间如白驹过隙,人生苦短,但是邓老的为学为艺,几乎影响了父亲沈邦武一生的书法之路,甚至深刻的影响了我们一家。我们三个兄弟沈必辉、沈必耀和我现在偶涉绘事,既有父亲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也和自小有机会亲炙像邓老这样的一代大家作书作画极其相关。
杨树谋的郑重推荐
父亲热爱书法,并没有家学的庇荫。童蒙时期,父亲出于自发,喜好书法。上学后,看到能写毛笔字的老师就更多一些亲近。尤其是在旧年的腊月里,写得一手好字的老师经常被人邀请挥写春联,大红的对联挂在家家户户的门两边,就是对书写者最高的奖赏。父亲下决心做个书法家,应该是在这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偶然被墙壁上张贴的“书法培训”广告吸引。那个时候的马路广告,不过是通过雕刻蜡版油印,而此幅的不同凡响处,则是完全的手写,一手漂亮的颜体楷书,落款杨树谋。
父亲其时正在自学颜字,又在渴望知识的年龄,特别向往有一个内行专家指点迷津。而这副广告,恰如一场及时雨,给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的父亲莫大的鼓励,他愿意花钱带上自己的作品,去找个真正的老师好好深入的学习书法。
一个周末,父亲准备好一批平日的习作,骑上破旧的自行车,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很方便的寻访到了居住在江汉路花楼街里弄的杨树谋先生。杨先生展开父亲精心准备的作品,端详了一会儿,迅即把他的杨五敬等三位公子找来,出乎意外的说了三句话:
——“你们看看别人写的字,再看看你们自己的作品,还不好好用功去?”
——“你到我这里来,我很欢迎,我不收你的钱(培训费),但我也不教你。”
——“你最好能够去寻访住在六渡桥大董家巷17号的邓少峰先生,他是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
父亲打躬在旁,将眼前这个50岁上下、言谈举止颇有些奇怪的老头的话默记在心。而——邓少峰,这个陌生的名字,第一次被父亲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在父亲临走前,杨先生专门展开纸笔,正经儿八百的现场写了一幅颜字送给这个登门求艺的学生,算是见证了一次师徒奇缘。作品写在一幅事先描好了朱丝栏方格的宣纸上,字体是工工整整的勤礼碑楷书,内容是那个时期最时尚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多年过后,父亲对这次与杨树谋先生的见面依旧记忆尚新、充满感激。父亲在杨先生的指点下,很顺利的见到了邓少峰先生,在大董家巷那个爬满了牵牛花藤蔓的老屋里,父亲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书法之旅。
杨先生在此后几年的文革时期,以老病之躯被驱赶到“知识分子下农村”的时代洪流中。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在邓老家的请益
父亲拜在邓少峰先生门下,眼界大开,学习的面自然广博许多。父亲记得第一次将作品展开给邓先生请教时,邓老先生针对他流畅的唐楷,只说了四个字:
——“写慢一点”。
邓老先生是习北碑的大家,对余绪于贴学传统的唐楷模式自然不习惯。这个脱口而出的四个字,也十分准确的透露出邓少峰先生“浑厚华滋”、“重拙厚实”的书法审美观。
尽管如此,邓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他依据父亲的特点,郑重其事的推荐了张旭、怀素的经典作品,而颜真卿,则不光是楷书了,更有《争座位》、《祭侄稿》等行草书作品。整个60、70年代,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父亲在颜、张、怀三家的门庭里锻造本领,为他日后因感情深远、胸怀坦荡、情绪充沛之性格而形成的深稳郁勃书风打下了基础。很多人都说父亲怎么没有直接去取法邓先生的书法风格?我以为,这恰恰是邓先生的高明之处,也是作为一个书画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他能够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囿于门户之见,这在当年缺乏正常书法教育的年代是非常罕见的。父亲的书风成熟得很早,特别是邓老能够直接点出父亲书法直接师法张旭、怀素,应该说,为他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书法语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个时候,经常去邓老先生家串门的老一辈艺术家有微雕工艺美术大师陈波涛、著名书法家黄亮、周华琴、陈义经、岭南派著名画家陈志宏、著名篆刻家杨白陶等老一辈书画艺术家。他们在一起,经常是一边吸纸烟一边聊汉韵京腔,颇有些名士风度。
邓老招待客人主要是纸烟,但凡客人来,邓老总要从他的手提小箱里摸出一包纸烟,轻轻放在桌上由客人自己取用。而客人来了,也只准现场吸,不准带走。但这些,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邓老家经常是高朋满座,也经常挑灯夜话,那个爬满了牵牛花藤蔓的老屋里也经常是烟雾弥漫,既有老朋友之间的互相过访问候,也有书画艺术的交流,更有瘾君子之间不为外人所道的快意空间。
这种待客的方式,放到现在不过稀松平常罢了,但在物资极其匮乏的60年代,在大家都在为吃饱三餐饭的时代,却显得极尽奢侈。父亲记得,他吸的第一口烟就是在邓老家。他先是从旁在侧听老先生们摆龙门,老先生们聊得越起劲,烟也就会吸得更来劲。这时,老先生们也会给父亲递上一支,父亲拗不过,索性自己也吸起来,以后更是养成了吸烟的生活习惯。
那个时候只要是到邓老家做客,几乎天天都能吸到牡丹牌香烟。
陈波涛请客
父亲在邓少峰先生门下学艺几年,邓老也对父亲格外看重。只要来客,总要父亲过来帮助照应。只要有宴席,邓老坐主席,父亲就总是坐在东角第一席的位置上。按照中国人的宴席传统,左尊右次,邀请人坐中间的上位。父亲作为晚辈经常是受邓老的直接委托,坐在东角第一席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老一辈和邓老年纪相仿佛的老先生们来访,父亲也总是在这个位置上替邓老安排招呼,完全显示了邓老先生对父亲的抬爱和垂青。
60年代末期,武汉美术界有展览,邓老先生是主要召集人。父亲只是向邓老学习书法,很少参与美术界的活动,也自然没有把这次美术界的展览放在心上。
有一天,陈波涛老先生专门托人来请父亲,邀父亲过府上小会。陈老是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是建国后湖北省首位微雕艺术大师,父亲感觉事情重要,骑车径直赶到武胜路陈老府上。但陈老似乎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先只是喝茶,接着是吃酒,父亲纳闷,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但又拗不过陈老的面子,不敢径直就问。
酒过三巡,父亲的直脾气来了神,实在忍不住,就向陈老请益——“您老有什么话就直接吩咐,不必兜圈子”。
陈老这个时候才借着几分酒劲说起了展览的事情。原来,由邓老任主持的这次美术界的展览,所列的名单中间并没有陈波涛老先生名字。而陈老又极有参展的愿望,并希望通过父亲向邓老转达致意,并且让父亲向邓老捎去“没有绿叶那能够衬托出红花”的道理。
父亲当然不敢马虎,都是前辈艺术家,自当认真完成任务。急急忙忙赶到邓老家请示,并原汁原味的将陈老的话转达给了邓老。邓老是个艺术眼光很高的人,又素来坚持原则。但这次,却在父亲的居间协调下,同意了陈老准备作品参加展览,而邓老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不愉快。
涂全模骑车追考生
1973年春夏之交,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从报纸上读到武汉市工农兵美术厂招聘画师的广告。工农兵美术厂就是现在的武汉国画院,上世纪70年代后一直隶属于武汉市二轻工业局,专门从事中国传统书法、国画和工艺品的创作和出口,在计划体制下,为武汉市创收了大量外汇。
父亲其时正在武汉市无机盐化工厂工作。枯燥的化工工作显然和他热爱的书法艺术完全隔膜,而这次广告则给他带来了转变生活的可能。
考试很顺利,先有书画理论考试,再有实际操作,父亲和另外一名参考者、著名书画家姚励群先生最终进入了决赛圈。所有的考试完成后,有一位中等个子、体型微胖的考官似乎意犹未尽,加试了一道题目——在你心目中,谁是武汉市修养最全面的书画家?谁又是修养最为不足的书画家?
父亲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思索,几乎是脱口而出——“修养最全面的书画家当然是邓壁邓少峰先生,那位齐白石先生在汉上的唯一弟子最为不足”。
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不科学是明显的。书画不是体育竞技,丁是丁卯是卯,一清二楚。尤其是书画艺术修养都在相当层次上的书画家,更不能够用这种竞技比赛的思维去排坐次、分高低。这么说来,其实父亲的回答也略显逡急,只是借这个场合,表白了他对邓先生的无比崇敬和感激。
父亲回答完就往外走。当年的工农兵美术厂在中山大道老法院附近,父亲考试出来已经步行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面有人在喊——“刚才考试的同志停一停,刚才考试的同志停一停”!
父亲扭头一看,一个干部模样的同志骑一架自行车向他追来,停到跟前就是一句话:“这位同志,你被录取了,下个星期一就来厂里报到上班”。父亲感到很迷惑,你是谁我不知道,又没有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要是按你的说法去上班,我又该去找谁呢?那个干部似乎看出了父亲的心思,接着说了句:“星期一上班,你就说找个姓涂的人,美术厂就一个姓涂的”。
后来的情况证明,父亲确实正式的被美术厂录取了,他也是唯一一个在这次考试中被录取的考生。这次考试,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他从此完全走上了专业书画的工作岗位。在70、80年代,父亲创作的上万件作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为武汉市创收了大量外汇支持地方建设,也为继承发扬书法传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个骑车追考生的干部就是当年工农兵美术厂的书记涂全模,而在考试后意犹未尽加试题目的考官不是别人,正是齐白石先生在汉上唯一弟子的哲嗣,当时任工农兵美术厂副厂长级干部。
79年的展览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三年后的1979年的秋天,为了歌颂伟大光荣的党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全市在中山公园举办具有展示全市各界人士拥护我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武汉市各界人士书画篆刻展览。
这次展览是在结束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市性的大型展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武汉市老中青三代书画家基本上都参加这次大型的展览,父亲不敢马虎,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在展览前父亲与邓老的闲聊中,偶然聊到这次意义十分重要的展览。邓老十分关心的问道:
“邦武啊,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送去了”。
“送了几幅作品”?
“两幅都送过去了”。
“那你认为谁的作品会挂在最前面呢”?
父亲笑而不答,只是望着邓老先生。邓老觉得有些奇怪,就又追问:
“谁的作品会挂在最后面压阵呢”?
父亲还是笑眯眯的望着邓老,邓老更加觉得奇怪了。
“怎么,你猜不到”?
父亲摇摇头,有点得意的说:
“我想啊,如果不出意外,我的作品最有可能挂在您说的这几个地方。”
邓老觉得很诧异,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父亲,心想——你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谈话当然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邓老的疑惑当然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内容大于形式的环境里,一切文艺都是为政治服务,这似乎也成为我们对文艺习以为常的一种认识。
展览当然如期举行,更重要的是这次展览得以让父亲的书法声名鹊起。原来,父亲的两幅书法作品都进入了展览。作品创作得相当出色当然是重要因素,而作品的内容紧扣了时代主题,应该是决定性的。一幅被放置在整个展览会的最前面,内容是用行书写就的新修改的《国歌》——“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另一幅则放置在整个展览的最后面,也用行草书写就、内容是铁人王进喜的一句名言——“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这一前一后同时为父亲所书的作品,一时引起武汉书画界的轰动,沈邦武这个名字,也从此被郑重的记录在武汉书法艺术界的历史上。
事后,邓老专门招呼父亲府上小酌,夸耀父亲会动脑筋想点子,要再接再厉,发挥长处。而邓老的老朋友们,那些经常在邓老家往来的老先生们,也都来向邓老表示祝贺,祝贺邓老教学有方。学生出手不凡,老师面子上当然也格外光堂。
也正是在此之后,父亲也有了最初的几个学生,比如王军、马锦堂、雷国栋,以及稍后的陈艳荣。
在武汉市教委的一次讲课
1979年初,武汉市教委邀请邓少峰、金月波、曹立庵三位老先生为全市的中学语文老师讲书法课。
其时很不凑巧,邓老身有微恙,无法前行。教委的同志就征求邓老的意见,请他推荐一名老师去授课。邓老没加任何思索,向教委郑重推荐了父亲。
教委的同志又来到金月波先生家,恰好金老先生也身体不适,不能够前往。来人觉得无法回单位交差,也如法炮制,要求金老推荐一个人参加讲课。当其时,金老先生也是父亲在书画诗词方面的老师,金老也不假思索的向教委推荐了父亲。
最后,教委在权衡老先生们的意见后,定下了授课老师的名单,一个是曹立庵先生,一个是沈邦武先生。
讲课如期举行,曹老德高望重,先上杏坛布讲。曹老讲执笔的力度时,强调要把笔握得紧紧地,只有笔握得紧,写出的书法才见力道。这是专业性而且争论很大的问题。最早的来源应该是王献之学书的故事。
王献之七八岁时开始学书法,师承父亲王羲之。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影响深远,很多习书人对书写时执笔方式、执笔力度的认识,都基本上来自于这个故事。
而我们知道,王羲之从学于卫夫人,卫夫人则有书字“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的理论,王羲之对其子握笔牢大加夸赞,应该是源出于卫夫人的书法思想。但事实上,在历史上早就有人对这个观点提出了疑问,唐代的张旭说书法“妙在执笔”,已经对执笔的力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宋代的苏轼则是直截了当的谈到书法“不在于握笔牢,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也就是说,如果要把笔捏得死死的才能够显出书法的力道,那么力气大的人就完全可以来做书法家了。这种揶揄式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书法与执笔的关系——在心理感受上得到的线条力量感,一部分确实来源于握管直书的力度,但并非正相关,重要的是要能够体会到巧力在书法中的运用。而这一点,则被宋代的大书家米芾点出——“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乎意外。”巧力对于书写后的效果,是“振迅天真,出乎意外”。有更多出乎意表的东西,才使得书法有着不同一般的吸引力。
父亲当然听到了曹老的观点,走上讲台,他也滔滔不绝起来。当有人提问说到书法线条的力量感和执笔的关系时,父亲很机灵的打了个比喻:
“书法执笔的力度,就像骑自行车,在不会骑的时候,手总是握得紧紧的,当你应付裕如的时候,力量就不是关键因素了!”
这个比方引来了隆重的掌声,父亲自然高兴,但此时的曹老却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学术上的争论,直接影响了曹老和父亲之间的私人关系,道道地地是父亲始未料及的。
一件明显的模仿作品
1984年,湖北省举办省书协成立后的第一届书法作品展。当年的作品展览实际上也是一次资格展,只有评选上了这次展览并公开展出,便可以加入湖北省书法家协会。这个资格条件是解放后、改革开放后破天荒的第一次,方方面面参与的积极性都非常大,父亲也不例外。
父亲创作的是一幅行草书中堂作品,内容是郭沫若先生的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度,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父亲记得,这幅作品到最后评审的时候,9个评委有5个评委打了入展的票,刚好过半数上了展。另外有一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完全模仿邓老六朝魏碑的写法,则是全票通过。作品书写的内容是杜牧的名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展览开幕后,父亲很较真,为了看这件作品,独自去了三四趟,仔细辨认。最后父亲认为,作者是在邓老写好的作品上,通过双钩的方法填出来的,所以作品的外形惟妙惟肖,而用笔却稍嫌怯弱。
恰好在展览期间,湖南有位诗人过访汉上,专程拜访邓老先生。邓老还是老习惯,叫来父亲做主陪,并邀约陈义经先生作副陪。席间大家觥筹交错,酒酣耳热。待到酒过三巡,陈义经先生就问父亲:
“邦武老弟啊,你在邓先生家这么多年,也算是老字辈的学生了,应该也在带学生了吧?”
父亲不假思索,当着邓老先生说了句:
“是啊,但是女学生最难带,因为她如果写不好,还得要你教她怎么样双钩”。
这句话当然是酒后吐真言了,父亲认为这样双钩的作品居然还以全票通过参加展览,对其他完全出于自身创作的作品,显然有失公平。
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邓老先生显得极富名士气,早已在酒桌旁鼾声如雷了。
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个邓老晚年所收的女学生,现在已经旅居加拿大。
我们三兄弟的节日
从1976年开始,我们家就在航空路、宝丰路一带搬过六次家。每次都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在一个地方的不同住地搬来搬去。计划体制下的房产管理,是分房和换房的关系,分房一次性,换房无数次。这个搬家的记忆,总是在脑海里盘桓不去,实在是太多了。儿时好些个自己喜爱的小物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溜到了哪里?每一次都感伤无数。
但我们三个兄弟觉得最高兴的,则是那几年的过大年。除了可以在新年里穿上新军装、吃上久违的大菜外,还有一件事,则深深的影响了我们,那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二,邓少峰先生总要到我们家回访。
父亲是年年的三十夜都到邓老家守夜,而自1976年后,邓老几乎年年都在大年初二到我们家过年,无论我们家搬到哪里,一来就是整整一天,一画也是整整一天。
应该说,我们弟兄几个直到现在还偶涉绘事,和当年邓老直接在我们家,给我们做现场的示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些年,物资极端匮乏,过新年能够吃上饺子,就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了。邓老到我们家过年,父亲有时也会叫上孔可立先生夫妇。他们是北方人,很擅长包饺子,又会调馅,总能够调制出正宗的北方口味。
应该是1981年,邓老照例在大年的初二来到我们家,照例整整一天就在我们家里,也照例画了整整一天的画。我记得,最早对国画中的矿物颜料的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最早对写意画的认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最早区分开行书、楷书、草书、篆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邓老喜欢吸烟,有时候甚至一边画一边吸,香烟把眼睛薰成了一条线,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呛得不行。邓老有时候整理分叉的笔锋,直接就用嘴巴。他有时候一边用眼睛直直地盯着画面在动脑经构思,一边把染有颜色的毛笔放入口中慢慢整理,嘴巴经常被染得五颜六色。
就是那一年的新年,邓老为我们三兄弟每人画了一副画,都题了上款,要我们雅玩、雅赏什么的。那是极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可以说,我们几个弟兄真正立志踏上书画之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是从临摹邓老先生给我们的作品开始的。
其时,父亲也给我们三兄弟做了个简单的分工,大哥沈必辉主要学国画,二哥沈必耀主要学篆刻书法,我呢,实在太小,父亲就说你喜欢哪样就干哪样。多年以后,还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我们学习书画篆刻的脉络。大哥学画主要从临摹邓老作品开始,又下功夫学习了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已经有着相当的笔墨功底。二哥的篆刻也是先从学习邓老的篆刻作品起步,直至上溯到汉魏碑版,最后定型到明清流派印的大师黄士陵,书法则是大量临摹了汉魏六朝作品后,将主攻目标定格在明清书法,尤其是傅山王铎。我自己则因为年龄的缘故,几乎没有能够和两位兄长在书画的技术上齐头并进,但这颗从艺的种子,早早已经埋就。
2010年9月稿于凤凰城
责任编辑:书法艺术网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书法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书法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相关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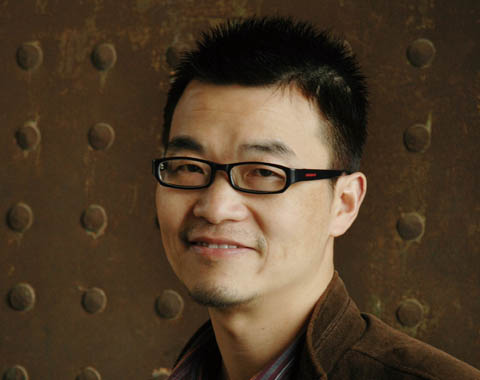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