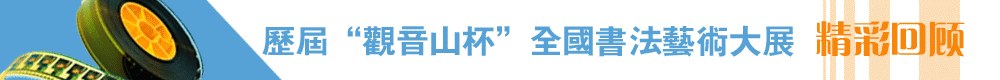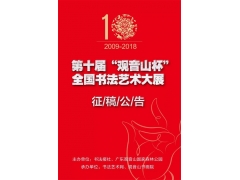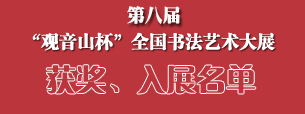从藏锋的原期再伸延,于是又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技法要点:在每一线条的运行中,不但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仅仅取藏又是不够的。于是后人又对之进行了义无反顾的追加:从藏到逆:口诀谓之“逆入平出”。
藏锋相对于用笔的行进方向而言,未必都是逆的。逆者反也。将欲与之、必先弃之;将欲行之,必先留之;当然在书法上,它表现为是“欲横先竖、欲竖先横”,看起来十分矛盾,其实却蕴藏了一个十分辨证的道理。
逆入的“反”当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技巧动作而存在。如果说,在隶书的石刻或墨迹笔划中我们能看到对起笔的回锋要求一一它就是逆入的基本含义的话,那么到了清代碑学家手中,“逆入”不再是一个简单笔画的形状,而是一种审美规范的表现。相对于帖学的柔靡轻滑或挑达而论,“逆”的含义即意味着强力、振作和沉重雄浑,它的风格涵义已远远超过作为技法现象的涵义。但毫无疑问,它是以技巧的“物质”存在为前提的。于是在北碑的雄强悠肆的审美需求映照下,逆入几乎成了明清时代书家的基本功内容。从王羲之的顺势以取妍到伊秉经、何绍基直到吴昌硕的逆笔为主,我们看到了一种审美观的变迁。它的深度显然比一个回锋或藏锋要明确得多。
“逆入平出”的原则看起来是针对线条的起迄部分,实质上,它却是意在线条的中段。记得清代碑学理论家包世臣针对唐以来书家论技巧只以线条的头尾起迄来判断优劣,而明显忽略线条中段的审美价值的弊病,曾提出一个划时代的理论标准:“中实”。他认为:真正判断一个书家的线条功夫,既不是仅看他的起迄动作如藏露,也不是翻的衔接动作如转折;而应该掩其两端玩其中截:如果中段是扎实有力、不虚浮轻薄的,那才能说是真正的功力。的确,自唐以来,由于颜真卿作为一代大师的功绩与影响,又由于他在技法上对线条的头尾与转接有过第一流的开拓,后人屈于对他的崇拜,往往只沿着他的思路,将用笔的起迄转接作为检验技法程度的唯,标准一-事实上这些部分也最明显、最易检验。包世臣的“中实”理论,正是对此的一种历史性的纠偏。要判断“中实”或’‘中怯”,难度颇大,又没有现成的传统模式可供参照,自然就更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了。倘若包世臣没有对北碑书法的彻底领悟,而只是陷入唐宋书法的审美格局,他未必能有此睿识。
以中实思想为契机,在“逆入平出”理论中还有一个标准:“涩”。“涩”者不顺畅也。它也是旨在保证书法线条的内在而不挑达、稳健而不轻滑:如果说“中实”是立足于书法欣赏或批评的角度,旨在作品对象的评价的话,那么“涩”则偏重于创作者主体的直观感受。前者指向审美对象,后者指向审美主体,互相吻合.即是对“逆入”的最理想的技法阐释了。
相关文章
- 薛元明:笔法杂谈2014-08-13
- 薛元明:谈结字2014-08-13
- 名家谈国展创作——陈海良2014-08-08
- 名家谈国展创作——汪永江2014-08-08
- 名家谈国展创作——张建会2014-08-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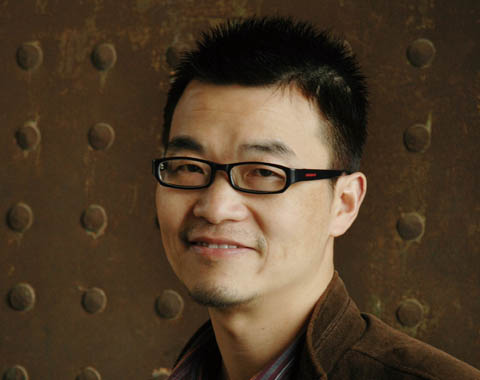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