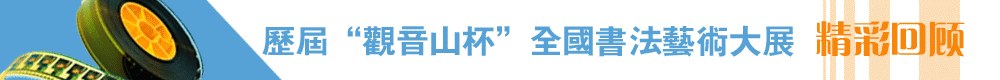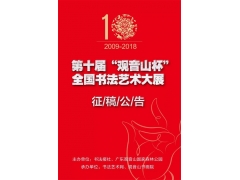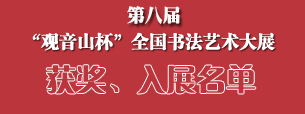沈延毅,字公卓,号述菊,晚号天行健斋主,作书亦属攻昨、攻昨老人、沈著等。先生1903年12月生于辽宁盖县(现名盖州)一个书香门第,1992年2月辞世于沈阳。先生早年曾就读于民国大学、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吉林道尹公署任职,旋即任中东铁路督办秘书,光复后任东北生产管理局秘书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员、沈阳市文史馆馆长、辽宁省政协常委、沈阳市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00周年,笔者不揣己陋,试论沈延毅先生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兼就梅墨生先生所著《现代书画家批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中《沈延毅》一文部分观点与梅先生商榷,并以此文纪念书法史不该淡忘的沈延毅先生。
沈延毅先生有人将其定位是现代书家,也有人将其定位于当代书家,因为其对书法虽有当代人的创作激情,但他的学书经历、知识结构、书法艺术思想基本上难以脱离清末,尤其是民国以来传统的书法模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书坛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书法热兴起后,他已走向人生的暮年,艺术也早已定型,当代书法创作各种思潮,基本上没有对其产生什么冲击或影响,所以对这位“遗老”式的人物,我倾向于第一种,认为他应该算作现代书家,或者说他是民国书家,如果说他是20世纪书家应该更精确。
一
我的第一个和梅先生不同的观点是梅文认为沈延毅是20世纪以来的重要书法家,我则认为沈氏是20世纪以来的杰出书家。梅文说,“本世纪(20世纪)以来的许多重要书家,只要是写碑的,总是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来自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数家的书法影响与传递,王蘧常如此、沙孟海如此、胡小石、张大千、徐悲鸿、萧娴都如此。沈延毅亦如此。”这段话,表明梅先生认为沈延毅是本世纪以来的重要书家,而且是和王蘧常、沙孟海、胡小石、张大千、徐悲鸿、萧娴并称的。沈延毅先生的书法是沿着清民以来的碑学风气而来的,但是沈氏对北碑的熔冶、驾驭绝非一般人可比。沈氏遍临北碑,深入堂奥,卓然独立,自成家数。聂成文先生发表在1994年《中国书法》第三期的《不使龙门擅伊洛——沈延毅先生的书法艺术》一文中对沈氏书艺从点画、结字、用笔到整体风格概括十分精辟透彻,现将其摘抄如下:
沈延毅先生的北碑,以方笔为主。源于史平公、杨大眼、孙秋生等名碑名墓志。风格方峻古拙,豪迈率真。起笔多切锋入纸,如断金切玉,然后转笔铺毫劲写,如锥画沙。捺笔多侧笔重按折送,如大刀般锋利。笔笔有弹性,笔笔见骨力,极富金石味。结字则以奇求正,字形方正而向左倾,开合纵横,尽随挥运。他还将篆隶笔意,行书笔意融入北碑,以行写碑,使碑写得更活脱,更富变化,更有韵味。康有为先生曾云,北碑“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沈延毅先生正是充分发挥了这个特点,将北碑写得极醇厚,极有神采,如老木杈枒,如万岁枯藤,高风标举,独具风骚。
沈氏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魏明伦语),写出了自己迥异古今的面貌,丰满了自己的艺术语言,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曾评价沈氏,“公卓以书法名世,有口皆碑,已有公论,勿待置琢”①,连启功先生在1984年为沈氏书法展览题词亦自谦“乡末”,并盛赞“白山黑水气葱笼,振古人文大地同。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比起碑学兴起某些人的泥古难化、局促做作或平庸滑腻,沈氏点画飞动,笔道迹痕点、线、块、面契合,雕塑感强烈;结字俯仰欹倒,挪让布白,奇中求稳,正中寓险;榜书大字、行楷中字、行草小字、蝇头楷书,从单字到整幅,皆臻妙境,尤其是行楷大字和行草手札,古往今来罕有其匹。
梅文中说,“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苏东坡、董其昌、王铎等书家的‘杰出’无不带有历史的微笑。不过,不能成为‘杰出’也不必过于悲哀,‘英雄’总是极少数极少数。问题是,‘平民’也存在着‘档次’与‘阶境’上的不同,……数千年书法的历史,这个‘阶境’的书法人物是绝对多数。这是不能也不必苛求于任何书家的。相反,我们都应该在期求‘杰出’出现的同时,认真地研究那些在这个历史‘象限’之下的有不同贡献的书家,确认他们的价值,为后人清理‘家产’。因为,他们是时代尖峰出现的基础”。王、颜等是“杰出”者,是“英雄”,恐怕无人敢质疑,然而,虽说沈氏等不是“杰出”者,不知是怎么比出来的?怎么认定的?笔者又从梅先生跨度很大,伸缩性颇强的语句中读出梅先生只认定沈氏是个相对于“杰出”、“英雄”的“平民”书家,且在“平民”书家中“档次”、“阶境”又很低,这又是怎么划分出来的?怎么认定的?以余拙见,“古人不见今时月”,沈氏之书个性特色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恐怕尚恨“二王”无沈法,若论气韵,沈氏与这些“杰出”、“英雄”有不及处;若论气势,与这些“杰出”、“英雄”未必逊之,也不知梅先生把自己比较认可的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沙孟海、李瑞清、王蘧常等等算不算“杰出”、“英雄”,梅先生心中那些“时代尖峰出现的基础”书家有多少人,大体上是哪些人物?笔者一直赞成“用作品说话”这个观点,如果近现代书家每人拿出十件、二十件代表作比一比,我看和沈氏雁行的最多当在十位左右,即吴昌硕、沈曾植、郑孝胥、康有为、于右任、弘一法师、谢无量、林散之、王蘧常?
二
我的第二个与梅先生不同的观点是梅文认为沈书比康(康有为)书逊色多了,我以为沈堪与康相伯仲,单就书法品格论,或谓过之。沈延毅是康有为的弟子,曾亲受其炙。沈鹏先生对沈氏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述——“先生十八岁时,亲受南海康有为指拨。其时,康有为寓居大连,先生经父执引见,康老示以唐楷之外,更应上溯汉魏,涵泳金石甲骨,庶乎有成;先生又得磨墨理纸于侧,亲睹康老措笔之妙,骇目惊心,深有所悟,窃心识之。临行之际,康老赠手迹二幅以志嘉勉。先生还家,遂理家藏旧拓,悉心揣摩,以为魏碑上承汉隶,下启隋唐,格高韵足,即以魏碑为根柢,兼参汉隶,时而临写,时而披览,时而书空画肚,朝夕斯者二十余载,直至年逾不惑,得两《石门》之精髓,爱其恣肆开张,飞逸奇浑,宜乎康南海之推崇也。”②这段文字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沈氏受教于康南海先生始末,以及在康氏耳提面命之后沈氏幡然有悟还家后调整书路之过程。梅文将沈氏与康氏进行一番对比,简介两者趋同之后,马上急转笔锋,得出结论,“应该承认,就创造的整体意义,沈书当然比康书逊色多了。沈延毅书法的明显不足便体现在审美风格——形式美感方面的结体造作与章法行气的不够浑整”。接着梅文另起一段又说“具体到沈延毅书法的价值评断何以逊色于康南海书法,这问题本身似不太重要,也不见得很难解释。沈延毅书法集中于行楷(这句话似乎未表述完整,应该再补上“较为见长”之类)——这是尚碑书法的一个特点。而在碑派行楷书中,其书亦不为出色,我以为这只能归结为书家的书法才情的不足了。能够将碑书写得自然和雅的有赵之谦、何绍基、沈曾植、康有为,还有于右任。他们皆能以中气贯注点画中。沈书则不能。”从这两段文字看,梅先生已经点明原本不想细究沈书和康书比“逊色多了”的原因,但同时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沈书“创造的整体意义”不如康,什么是“创造的整体意义”,书艺上的完全无古无今的“创造”是不存在的,康书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康氏对《石门铭》、《瘗鹤铭》、《云峰刻石》,特别是宋人陈抟的结字用笔借鉴良多,陈、康分别书写过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对联两相比较即是明证。康氏的书法理论也是在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基础上形成的,连书名也仅差一字,更鉴证其书、其论均非全盘独造。沈书从用笔到结字迥异时人,线条质量绝佳,结字险中求稳,稳中求奇求变,之于古人亦不可说其不是“创造”,至少难以说清沈书主要象谁,正如蜜蜂采蜜见蜜不见花一般。基于此,就“创造的整体意义”看,二者也很难说谁比谁差多远。其次,沈书“逊色”原因在梅先生看来还有两条:一是“在审美风格——形式美感方面的结体造作与章法行气的不够浑整”;二是沈氏“书法才情不足”,将碑写得不够“自然和雅”,不能将“中气贯注点画中”。那么我们不妨从梅先生指出的两点原因上将康、沈再稍具体一些进行一下比较:首先,说一下审美风格方面,就审美风格上看应该是“燕瘦环肥”无法说哪种风格更好,而再具体一些,说到形式美感方面的结体与章法行气倒可以理论一番。梅先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过康书,“康有为书法的风格,总体上是融会汉魏碑版摩崖于一炉,兼糅楷、隶、篆、行草体势于腕下,意态腾挪、气象开张、体势浑古、笔力雄健,亦奇亦险亦质亦古。”③笔者以为这段文字用来评价沈氏书法的风格也未尝不可,若细分,从兼取的继承上看,康书篆味浓一些,沈书篆味淡一些;从意态上看,康氏行草书动作大一些,行楷基本上很少有腾挪,沈氏则无论行草、行楷腾挪幅度都比康强烈一些;从气象上看,康氏行楷纵势横势开张均可,但整体气象不大,行草纵势较开张,横势则拘紧,故而字多行多的作品行与行之间呼应顾盼较差,整体气象受到一定影响,而沈氏则无论行楷、行草纵势横势均开张,且气象宏大;从体势上看,康书体势偏向浑茫,古雅不足,沈氏既浑且古又雅;从笔力上看,康书雄浑霸悍之外轻佻之笔亦不少见,且无论行楷、行草笔道之中变化较少,可能与其为书多用臂用腕少用指有关,沈书笔力扛鼎,且用笔如用刀,斩截沉着,积健为雄,且臂、腕、指并用,“时时‘翻毫’、‘捻管’或‘转指’”(见梅文),故笔力更强、更健,笔道更沉、更厚,变化亦丰富。从上述对比看,沈氏非但不“逊色”,且有过康之处,应该说沈延毅是康有为书法的“出兰”高足。另外,说沈书结体造作,似乎有失公允。北碑书法强调结字之奇是其一大特色,且沈书中融入欧、颜、柳及李北海,甚至王书《圣教序》之结体特征,其行草手札“二王”结字更为明显(如致卢树勋信札),胸中学养,流泻笔端,除个别作品中个别字外(哪个书家都不可能无缺憾之作、缺憾之笔),极少扭捏造作。如果硬说其书结字造作,恐怕魏碑摩崖和碑派书家犯此病者黟矣。
说其章法行气不够浑整,此语亦显偏颇。试看《沈延毅书法作品选集》中选入的(并非都是先生的好作品,有部分作品是在沈氏去世后不久很短的时间内从单位或个人收藏的作品中收集起来的,精品尚有遗漏)对联和少字书法,抑或多字条幅、条屏、横幅,或者是信手拈来的手札,笔酣墨畅,洋洋洒洒,浑然透脱,含英咀华,怎能说其“章法行气不浑整”?若说其中个别作品有此瑕疵尚可,全盘否定恐怕难以服人。
再看看沈氏的书法才情是否不足,是不是将碑写得不够“自然和雅”,不能将“中气贯注点画中”?不知梅先生是如何定义书法才情的?是指书内才情,还是书外才情。论书内才情,沈氏年少即始从隋唐入手,在欧、褚、颜、柳等下力尤勤,经康南海指拨后,主攻北碑,并上溯秦汉篆隶,近取何子贞,从三、四十年代以“沈著”落款的手札和行草书作看,沈氏学何,绝非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而是掺入碑法,行笔圆融厚朴,气韵儒雅贯通。亦殊为难得,非有书法才情难臻此境。五十年代《沈阳文史馆乔迁感赋唱和诗》小楷作品,结体清隽疏朗,点画劲健斩截,直逼魏晋,别开一境。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沈氏在文革中走“五七”道路,下放到辽中县农村插队劳动,亦偶或试笔,所书毛泽东诗词作品和一些自作诗词加入对生活的理解,更加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个人风格已经形成。“进入八十年代,沈延毅先生的书法艺术又进入了新阶段,进入了高峰期,艺术更加纯熟,造诣更加高深。就象他的年龄一样,进入了老境,进入了老笔纷披的境界,胸胆更加开张,笔墨更加老辣,更加随心所欲。”④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精品,《沈延毅书法选集》中选录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没有一定的书内才情,是难以达到几种书体皆工。魏楷与行、草结合自然,书风个性强烈的至高至难境地的。论书外才情,沈氏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秉承家学,从其父沈羹唐先生学习国学和诗文书法,沈羹唐先生是清末拔贡,颇有文才,亦擅书法。及长,沈氏又先后就读民国大学、北京大学,有较深的国学根柢,又长于吟咏,他的诗名在辽宁诗界是相当大的。诗三百烂熟于心,并对晋之陶元亮、唐之王摩诘、杜少陵、宋之苏子瞻、金之元遗山等诸家诗风偏爱有加。感慨人事、览物抒怀、读史咏志、雅集感会,往往赋成诗联,并以书记之,赠之同好。当代人写的旧作诗多不讲格律,不谙声韵,无情境,寡趣味,或语言陈旧翻版古诗,或语言俚俗难得渊雅之致。沈氏为诗作联绝无此弊,先生所作律诗均格高韵古,苍凉豪迈,意味悠长,雅逸中包孕壮美,寻常中凸现奇崛。如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后,所做《题全国书法辑》“虫鱼鸟迹溯源流,继往开来见自由。劫后一编新墨宝,书风再振古神州”。抒发了书坛万马齐喑后欣逢盛世的喜悦之情。由书事联想到国事,以小见大,颇见巧思。沈氏文革期间被下放到辽中县的农村插队,走“五七”道路,已近古稀之年,常于耕作之余,以诗书自娱,曾有诗为记——“误我虚华去日多,每思畎亩寄吟哦。老来重试田间味,犹记家山采采歌”。静观世事,笑对人生,娓娓道来,古风犹存。《题霍安荣遗著》“感旧怆凉已隔年,又从门士覩遗篇。愁来不待山阳笛,往迹回思一惘然。”睹物思人,情真意切,又巧用典故,更增悲凉。先生老友辽阳书法家、诗人陈怀《书法作品集》问世,沈老题诗致贺——“淮海有佳士,久居辽水滨。诗书开意境,风雨壮吟心。我亦垂垂老,君还冉冉春。铁辛(陈怀先生字铁辛)诗卷在,快读重斯人。”格律严整,平仄谐和,中间两联对仗工稳,语言平实自然,期望殷殷。沈老六十五岁生辰赋七律一首自寿“读罢鸱鸮岁又更,理参破立佩英明。琼瑶已去怀三宝,肝胆相倾重两生。夙夜在公难免过,同劳从众贵无名。朔风凛冽隆冬日,盛世期颐满一角黄 。”自述命途多舛,处之泰然,感慨系之。以上几首诗歌为证,沈老诗性文心绝非平常人可及。书外才情由此可见。说沈氏书法才情不足恐怕不足信矣。
说沈延毅书法不够“自然和雅”,其实有些强人所难。“自然和雅”应该是帖派书法的主要审美特征,刘熙载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⑤沈书当为北书一脉,自然以骨胜,故而得“雄健”而少“温雅”,“温雅”者与梅文所指“和雅”近之。然沈书又能取法晋唐,从其行草书札和行书结字上看,“二王”、李北海等对其影响甚深,以碑为根柢,化帖入碑,镕冶一炉,成自家气象。以用笔的沉厚跌宕避开了徐三庚的“轻滑”,以帖气入碑避免了李瑞清的“做作”,以碑的险峻、帖的灵气逃避了曾农髯近于馆阁北碑的“平庸”,以多变的用笔和写劲回避了陶氵睿宣的“刻板”⑥。正如当代书家魏哲先生所说,“沈延毅以碑名世,其用笔乃是真王”⑦,其书已有了法帖、尺牍的韵致,魏晋风度俨然存在。另外,记得梅先生在评价齐白石书法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齐白石生于晚清,书法观念上自然受到清人尚碑风气的影响,所以用笔上多侧锋方笔以取姿态并追求碑意。但如果我们因此认为齐的书法只向碑版及粗犷一路取鉴,而不能精秀典雅,似乎便错了。”⑧我看这段话将齐白石换成沈延毅未尝不可。所以我一则以为苛求沈书“自然和雅”有些偏激,二则认为沈书也并非完全缺乏“自然和雅”。倘用“自然和雅”来绳之梅先生文中认可的赵之谦、何绍基、沈曾植、康有为,还有于右任,我看赵的碑楷结字规整,用笔滑腻几可入电脑,“和雅”不错,“自然”稍远点;何之用笔抖动,蚯蚓式的线条,尤其收笔的细尖,“自然”稍差,“和雅”亦不到火候;沈过分求用笔生拙,火气未退,筋骨外现,转折生硬,显然不可用“自然和雅”来拟之;康书一味放笔,筋骨外露,缺乏渊雅;于书当此四字,倒无大碍,因其碑帖融合绝佳之故。
说沈书不能将“中气贯注点画中”,“中气”是什么?恕我读书无多,未见过此词,从字面上理解,好像应该是说沈书点画气势不连贯、不畅达,点画缺乏神采。仅举沈氏行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发表于1994年《中国书法》第三期封底)为例。整篇气韵贯通,点画行笔起伏流宕,精气内敛,“纵横屋漏痕,遒丽锥画沙”差可拟之。从正文到上下款字,戛玉鸣金,灵动自然。变化丰富多姿,奔蛇走虺,翰逸神飞。尤其是几个“点”,或如乱石崩云,或如惊涛裂岸。其条幅、条屏及行草手札自不待言。
三
我的第三个和梅先生不同的观点是,梅文中说沈氏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书家,我倒以为沈氏是个有“思想”且给自己书法风格取向定位准确的书家。梅文中说——如何衡量一件艺术品和如何评估一位书法家?“标准”因“观念”而异,“观念”因“思想”而生,“价值”当然由“标准”所得。问题是,作为创作家和理论家,你有没有“思想”?潘天寿说:“一艺术品,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这也是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前,被肯定价值所淡忘的当不只是沈延毅一位书家了。
梅先生这段作为本篇批评文字的结束语,开笔又异峰突起,弄了个设问,然后跳闪腾挪,似答非答,用了一串名词,兜了一个圈子,引了一句话,就此打住对沈氏的批评。在梅先生看来,按潘天寿先生定的“标准”衡量沈书得出结论——不“合格”,作为书家,沈氏“没有‘思想’”,核心问题是沈氏因为“没有‘思想’”所以才会创作出不“合格”的“艺术品”,因为“艺术品”不“合格”,所以书家本人也会被淡忘。那么,沈延毅作为一名书法家,他到底有没有“思想”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沈氏是个有“思想”的人。“思想”一词在《辞海》中有三条释义:一是思考、思虑;二是想念、思念;三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应该说沈氏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而且单就书法艺术而言,他有独到的见解,并能“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徐悲鸿语),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去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去寻找自我,形成自我。按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沈延毅,沈氏相去较远,从理论研究、理论建树上看,沈延毅平时对书学的研究心得除了在一些论书诗(如“举世千年赞墨皇,临池反复细端相。龙蛇入草苞元气,毕竟南王逊北王”,“十年磨墨墨磨人,费纸千张未得神。索本求源还上溯,方知篆隶是前身”等)中吉光片语得以展现,同时在课徒和主持辽宁书协工作,参加一些重大书法活动时即席发表一些见解理论,往往语言鞭辟入理,振聋发聩,切中要害,先生绝少长篇大论,更没有书法专著,这和康有为、沈尹默、沙孟海等主动地有意识地搞一些理论大相径庭。
相关文章
- 第八届“观音山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获奖书家徐右冰2017-06-05
-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2015-03-11
- 黄文泉书法作品2015-03-12
- 意趣横生 洒脱自然2015-03-12
- 把字写活了2015-03-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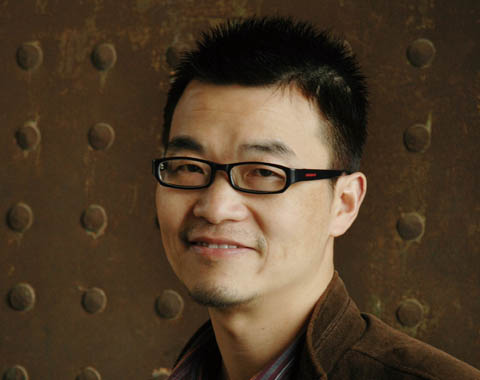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