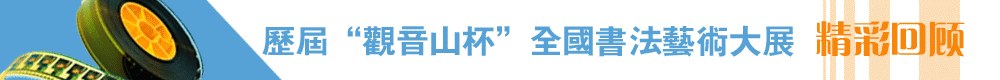冒孝鲁
冒孝鲁,景璠,如皋老狂人鹤亭诗人之子也,为北京某大学专攻俄文之高材生,任颜惠庆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有年。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外文教授时,余以鹤丈之介始与相识,觉其人之狂傲,有逾于老父。渠每读鹤丈诗文后,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邃于国学,故敢如此也。凡有自命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者、至多读三行,即云:好好,掷还了(忆先外舅况公,昔年黄公渚孝纾、龙榆生沐勋尝以词求正,原封未动,外批“至佳”二字还之。故黄、龙二人提及况公时,必大詈不已。孝鲁还读三行,似比况公略谦邪?)。湖帆平日以词自炫,尝亲书小楷,付珂[王罗]版影印(后附《和晏词小令》一卷,乃倩女词人周[金柬[霞代书而提刀者),名曰《佞宋词》,求孝鲁为作序。孝鲁以其老父至好也,故嘱湖帆求鹤老撰之。鹤老大窘,事后谓余曰:这词,做周女徒孙都不够格,真无从恭维之也。湖帆又坚嘱孝鲁作跋,跋成,竟莫名其妙。余后问之,孝鲁笑云:他词更莫名其妙啊。
但在丙申、丁酉间,渠以许效庳之介求太极名家乐幻智奂之医病,乐公以气功治愈之。他们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孝鲁自此遂乐老师乐老师不已矣。后告余云: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观此,则非对任何人都狂了。
孝鲁好色之登徒子,亦惧内之大王,但只要避了河东狮,艳闻逸史,层出不穷。知余解人也,故一暇休息之日,必光降寒斋,畅谈过去为乐。渠与余有同一心得,非可以言语形容者,即不问初觌面之异性,如何严肃端庄,如“心有灵犀一点通”者,一握手即可明白了,如对方不属意,则以严肃对之,庶免白眼相向了。他自俄回国时,尝畅游欧洲各国,以夫人不在,故艳事特多。不遑多赘,只述渠在法国时之一为例,即可概其余了。国少妇,至娟媚,未交一语者。下车后,伊人手提一旅行包,在他或前或后,微露娇不胜力之态。他按照外国规矩,趋前愿为代拿,伊人表示感谢付之。乃一经手提之,立即发觉内只衬衫丝袜而已,轻极了。明白了,即向她询问要否送至寓中?伊人遂即以寓所告之,并云:夫为某处某职,午饭不归家的,明午如蒙光降,当备午餐恭候如何。孝鲁允之,并送至门口,即彬彬有礼告退了。次日修饰整洁后赴会了,饭后遂成腻友那个那个了。其时,余有某剧人(名间南北大艺人也)委刻印章,以汽车迎余至其公寓中。时正七月,其禁脔亦大名坤角也,年可二十余,窈窕多姿,与余询问篆字不已。余迷之,次日特以许多作品示之。她仅着汗背心、短裤,竟半跪半侧身,傍余沙发而询一一,达半小时以上。余凝视其白皙皮肤,大约有痴状?为此大名角所见了,竟当时把她隔开,操其乡土语,喝进去了,并对余白眼相向,此伶,著名色中魔鬼,凡其班中坤角,无幸免,闻后房达六人之多云。余以此事告之孝鲁,孝鲁云:白眼相向,你亦应有“皮肤虽痛也风流”呀。说毕,吾二人大噱不已也。孝鲁虽好色,但于朋友之妻以及女学生从不作一非礼之事,此殆释家所谓上乘功夫邪?自其去皖后,即无音讯相通矣。其夫人余亦见及,固一大家闺秀也,殊和善,孝鲁畏之如狮,乃自作孽耳。
沈剑知
沈剑知觐安,八闽世家子,曾祖沈葆桢,祖及父不详。他为福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生,抗战前任江南造船所上校官,抗战后退隐了,居富民路富民新村多年。妻故世后,他遂与其长嫂刘氏同居了,房中只一榻也。嫂为故北洋派伪海军总长刘冠雄之女。刘胞侄亚文(南京戒烟局长)所亲告余者,云:刘氏中人都不齿此人者也。他擅山水,自云学董香光有独得之秘。又擅作诗,专学陈后山,为梁众异,李拔可、释堪昆仲所赏识,故狂到了目中无人矣。尝有一诗,为某诗人所推崇,面誉之谓,神似放翁之作。他竟拍桌大骂,谓放翁哪里及自己,诋此人为不懂诗云云。
汪伪时,上海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之妻黄慕兰(原大连妓,名黑牡丹,后当记之)正戒除嗜好,附庸风雅,聘陈师曾、陈半丁之得意女弟子江采南频授花卉,沈剑知授山水,入晚即以汽车迎江、沈二人至愚园路钱宅,供丰盛夜餐挥洒为乐了。向例,以生理上之关系,戒烟之后,性欲特旺,黄慕兰未能免之。沈遂与之大肆非礼了,后黄又为一为之戒烟之医曰苏记之者所占有,沈遂转移方向追求江了。江与沈对门马路之比邻也,竟日夕不离左右。江丈夫死后,沈益肆无忌惮了,竟不准江接见任何一个亲戚朋友了,使江大怒,竟与之绝。解放后,江考入博物馆复制品工场工作,沈借谢稚柳大办亦进了博物馆为干部,二人偶尔在电梯中相遇时,都别转了头各不理睬了。江与余至熟之友也,偶谈及沈时,都嗤之以鼻也。然江至今所画山水,几与沈无差别,足见二人当时之密切也。
在三反五反时,谢稚柳犯了错误,成十大老虎之一(见报者),竟致五花大绑,绑上舞台,宣判缓弄三年时,沈前据第二排座,频频起立拍手大呼以耻之(闻当时检举最为力者,亦沈也)。此均尹石公当时在大舞台参加时所目睹之事,后以告余者,当不诬也。故尹老对沈为人,殊鄙视之。稚柳谈及此人时,总大詈不已,应当也。沈对余治印,认为最佳,故为之所作不少,他贻画亦多,惜均随收随弃矣。闻近来他告徐生云,抄家发还东西,陈印尚存一二,为幸事云云。此亦余之知已邪?
有一次:似在抗战前,沈以所藏江西新城陈侍郎某某所书楹联二事,出示于梁众异,拟求售。陈某某(名偶忘,乃嘉道时著名写董字之名家),为陈病翁之曾祖父也,梁因之请吴湖帆、吴用威董卿(与冒鹤亭郎舅至亲,亦以摹董书得名)、陈病翁及沈等至家午饭,悬此二联,求陈等审定真伪。陈云膺鼎,沈云真迹,争之不已。沈忘却了宁有看错之理。病翁拍桌詈之云:这是吾曾祖书法,笈中尚藏多件嗣守,可以取来一比,宁有错邪。你不认识吾上代之字真伪,犹吾不能辨尊曾祖沈文肃公之字也。大狂人被老狂人所压倒了。故沈每谈及陈时,总有恨恨之意。但余曾以黄公渚、沈剑知之文字如何以叩病翁,病翁云:均不坏,但以二人均自满太甚,未肯更上一层楼了。陈作一比喻曰:他二人都已在国际饭店十四楼吃了精美之食矣,亦已据高可望见人民公园全景矣。如能更上至廿四层,则黄浦江与全上海可以一一尽入胸中了云云。此言虽谑,似有真理也。
陈蒙庵
陈蒙庵,此人与前二公迥然不同矣。他殆一世中从无二色之正人君子也。其狂放自傲之态,与二人略有不同,盖狂而有颠状,又口没遮拦,说后尚不知已闯了祸。他在况大先生处信口几句,害内子大病三四年之久,余与况大至今尚未释嫌,均其一句胡言,而有此后果者也。前已记之,兹不赘。兹忆在丙寅、丁卯间,余为之介绍与湖帆为友,湖帆以其况氏及门、颇善之。他一再嘱书,无不允者。后又屡代商人求书,湖帆云:富商之件,需叨光付润。他竟打了京片子说:“这,瞧您得起,给您写的呀。”使吴大怒,乃与之绝交了。他除况公几个知交如朱疆邨、冯君木、程子大寥寥数老外,其他至友易大厂、吕贞白为好友,袁伯夔、周梅泉、陈病翁等等,均不肯与蒙厂往来,都云:土膏店小主人,一身土头土脑云(视为乡曲之意也)。与赵叔雍二人,时时彼此奚落,余时时见之。但平心论之,文字似不在叔雍之下也,否则,圣约翰亦不致聘之为文学教师也。而他能挈况大作助教,且为之每日整备课文,每与函及文,总曰:某某教授兄。此则不负师门,余至今认为可嘉之事。第生平未至北方,与真正名士如溥氏诸昆仲,以及罗瘿公、杨云史、李释堪等接触,而一口北京话,即为甚是,以致于对袁伯夔、周梅泉、沈剑知等巨宦后裔谈吐进退之间,大有票友登台演剧,不甚自然,反不如若龙榆生、卢冀野前之一口的江西、南京土音为落落大方。惜蒙厂见不及此,为可惜耳。
吕贞白
吕传元(丁未生)贞白,江西九江人,父名鹿笙,以盐起家,任过一度小官僚,与夏剑丞为亲戚。少聪颖,读书甚多,故由夏公为之誉扬。又以十发老人为介,与蒙厂为至亲密之友好了,二人几无日不以作文填词为常课。当时(抗战前一年)南京路新雅酒楼下午二时至五时有点心座,冒鹤亭、陈病树、周梅泉、梁众异及其他诗人必每日去小叙畅谈,吕亦时时敬陪末座,他们亦颇青睐有加,以致效学了冒、陈、周三老狂人之形态,变本加厉,竟任何人不堪一顾了。吕因蒙厂关系,故与余亦至善。某日,余与杨虎之主任秘书江西南丰人赵某某亦一同至新雅小吃,为吕所见,过来招呼。余好意为二江西老表作介绍,赵君至客气招待,时赵正手持一书翻以解闷,吕据夺而观之,乃一清人普通笔记之类,吕以鄙视之目光谓之曰:“啊,你读这种的书,也可以做司令部的秘书吗?”赵大怒答之曰:“咄,你是哪里钻出来的小流氓,吾南丰赵氏,从来不知九江有姓吕的有读书人的。”言毕拍桌大骂小流氓不已。吕知难以斗杨氏部下,只能鼠窜而逃了。使余两面做人难。吕走后,赵犹向余叽咕不已也。自此以后,吕即不去新雅,蒙厂处亦总在白天去了,以余只夜访耳。从此竟无会面之机会矣。后闻况大云,吕、陈也交恶绝交了。
初,湖帆每填词,必请冒老改正,冒故后,又请中央伪大学教授汪旭初东润色之,汪死后,乃与吕为友,成至好,亦为改词也。岁甲午,湖帆始告余者,云:贞白每星期日上午必来。余以为老友好,某日早午特至吴宅,进房时犹见吕旁若无人,眉飞色舞而谈,乃一见余到了,立即云:吾头晕,吾头晕。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匆匆而去,湖帆认为此奇事,余已知他犹未忘新雅受辱之耻耳。亦未与湖帆言之。及六七年,始知他亦隔离中作牛鬼,乃汪伪时期某部大秘书也。吕寓延安路明德里,无子女,以惧内出名,始终不敢与任何女性为友云。但闻蒙厂昔年所告者,未知确否?
潘伯鹰
潘伯鹰,别号凫公,皖之潜山县人。抗战前无人知之者,胜利后始来沪,任伪中央银行秘书。始知渠在重庆时以凫公笔名写小说而成名者也,能诗,能仿文选作赋,尝为稚柳作《写竹赋》一篇,余曾见之,但未遑终篇,以用典过多也。又喜仿褚遂良之伊阙佛龛碑字体作书,因此得章行严与沈尹默之青睐,遂自命为第一流人物,狂放不羁矣。渠在重庆时所用印章佥为乔大壮所刻,来上海后,居然嘱余联襟冯宾符(君木之次子)为介,光降寒舍,一见如故,畅谈至久乃去。他与稚柳二人最为莫逆。名票张伯驹,收罗溥仪自长春出走后所遗失之古画特多,如陆机墨迹《平复帖》、徽宗《寒鹊图》等等。每得一件,必至申请稚柳、伯鹰赏鉴,同时有吴某某、刘丕基(靖基之弟)亦厕其间,于是他们五人互相宴会,余无一次不作陪飨者也。伯鹰最豪于谈,而体力雄健,仅次于大千。他除却章、沈、张大千、谢(书画也)、张伯驹(收藏大家也)及余(刻印也)之外,以陈蒙厂为况六弟子,又与其夫人为同乡,故亦甚知已,但从不请陈同席者。后余始知伯鹰尝介蒙兄与稚柳为友,稚柳与谈二次即恶其人,谓太萎而小派,声明不欲再见之故也(大约又是一口京片子,稚柳吃勿消了)。除此之外,竟目中夫人矣。故遂公认可列入十大狂人之中了。余认为他虽狂,豪爽为其优点也。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
他夫人亡后,一度追求一女画家(悟空同宗妹子,亦名媛也),不遗余力,在五六、五七年之间,不知闹多少笑话,几乎传遍了书画界,以致好事不成。后此女嫁与富人吴某某,伯鹰徒叹奈何而已(因此女有三个油瓶女儿,日需五六元营养品,开价每月须三百元家用不可,以致中断者云云)。后又娶一位全家老小有五六口之多的年约四十之徐娘为妻了。时五九年后之事,余已去淮南了,故未详何以结合者。及六二秋,余回申后,乃稚柳告余者,并知他已任上海市府参事,兼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沈正主任),并已有自北四川路迁居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正对门)。时沈玉还与潘已至熟,且为会员矣,余乃随他同访潘氏,直趋卧室,见他已横卧床头,云正从华东医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谈为乐。并介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当如虎之年之娇妻,安得不病乎。时余询以何时乔迁至此,他大笑云,这是岳家呀,吾现在是做了猪八戒,入赘在高老庄呀。时余正患腹水肝硬化,腹大如瓢,知他亦以肝炎转腹水矣,故笑答之云:吾与你都大腹如鼓,是吃了女儿国的水了吗。互相戏谈为乐,后忽严肃地劝余云:某某,吾们都患了这不治之症了,今日是高兴,将来临终时是痛苦万状的呀,望你学学吾,多卧少动,希苟延残躯吧。余笑谢谢而已。其后在稚柳处迭闻其屡进华东医院不已。在六四年余又去华东观之,已神志颓然,告余曰:在此,虽号称最高级医院,但区区小官耳,不过初出道少年诊病而已,而且清规戒律太多,急欲归家了。自此以后,不能见客矣。至六五年,闻弥留达两个月之久,死时全身漏黄水满床第,亦惨矣哉。后闻他与蒙厂也偶因谈文不合,而绝交者。在余谪居淮南时,他出全力以捧高式熊达三年之久,所有篆刻诿件,及友朋所嘱,均一一介于高君者云云(他甲辰生者)。
许效庳
许效庳,德高,丙午年生。镇江世家子也。祖汝棻,清进士,官福建官铁局总办,与郑苏戡为至交,尝以书苏戡之介,至天津张园授溥仪书。后许任副大臣代部了。父经农,清癸卯举人,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月六十五元者。效庳自幼至长,全为其祖父所亲授文学者,性聪颖,最擅作诗,又为苏戡所赏识,时予指正,许为佳子弟,故养成了他狂傲不羁之恶习了。
许在十余岁时即入上海交通银行为小行员,以诗文关系,为行中发行处长吴眉生庠(亦镇江人,擅诗、词、曲驰名者)所赏识,妻以侄女(江采女士乃眉翁之弟妇,效庳叔岳母也)。及抗战后,其祖虽已故世,但日人竟以中日合办“华兴银行”之经理一职任之了。所以沦陷八年中,他为最趾高气扬之时也,汽车阶级了。胜利之后乃一蹶不振矣,解放后,益穷困。子女四人,相继入党,一见面即以正义劝导重新学习做人。他竟置若罔闻,日至江采家闲谈而已。余于其时始与相识者。及其父进文史馆后,月给十元作零用,遂日至书场以听书作消遣矣。是时余以戒除嗜好,亦无日不以书场为消遣,遂与他更知已了。余学集句,盖得其指导为多也。是时据其自言,只陈病树、汪旭二老为其所崇拜之人,陈亦最与之知己者,若吴眉生、陈蒙厂,尚认为可取,沈剑知、潘伯鹰、吕贞白,则无一人其目中矣。他云:女子中二人为佳,一为陈小翠,评之曰:惜诗中用成语过多一些;二为周[金柬]霞之小令、绝、律诗。有佳句可称女才子云,故与周二人至亲近,周亦径呼效庳效庳不已(余所介绍二人为友者)。周语,略有江西腔,读“效”作“小”,“庳”作“鄙”,故缪子彬一见他,即谑之云:“小鄙”来了。他亦怡怡自得。余听书只盯住沧洲书场一家,他听书,专盯住一个女艺人名侯莉君者,侯至哪里,他即在哪里,侯去外码头,他即休息了。他为侯一而再,再三四赠诗不已,以为可得美人青睐了,可怜侯乃一目不识丁之人,常对之瞠目不知所谢了。此诚所谓单相思,发魇耳。故余尝告病翁云:效兄,狂之迂者也。子彬云,他真是穷星未退,色星高照者矣。后其父逝世,生活益困,赖子彬十元五元接济。余为介绍作一小序,润五十元,他仍乐于此不疲也。一次,竟与余闹翻了,事实可笑已极,他曾告蒙厂云:黄静芬女艺人弹琵琶最佳,可属其演奏一曲以供赏娱。蒙厂允之。事为余所知,正恨内子大病卧床均陈所闯之祸,故即告之黄女曰:你不要弹,陈某不是老听客也。黄女亦平湖人也,当然不弹了。是日上台,即推手痛婉拒了。他至后台责黄失信,黄云:某某说不要弹呀。他大怒,竟属不知何人画了一手卷,曰某某某图,丑诋余霸占黄女,蒙厂首为题词,汪旭初、吴眉生、陈病翁均亦题了。他以示江采,求书引首,江力劝并为吾二人解劝,余云:与蒙厂作戏耳。许乃立即撕去其图,言归于好了。后子彬笑谓余云:陈病翁诗中讥讽其吃醋失败,故不得不撕去了。
至五七年秋,他以郁郁患喉癌逝世了。在五月初,他生日,已自知不起矣,病翁特设宴宽慰之,次日作七律一首以谢,前六句已忘却,后二句云:“赤脚层众吾自愿,眼前泥潦况纵横。”绝笔也,衰退至不忍言矣。后其友陈文无名珂收其遗诗油印一册贻人,病翁为作序,伤痛不已云。他尝告余曰:人都说吾狂,吾对散原、苏戡、众异、病树诸公之诗,即自觉珠玉在前,低首甘拜下风者,其他名人都不是高手,故不敢赞同,吾何尝狂邪。此言或亦有理。
白蕉
白蕉,丁未生,字复翁,本姓何,松江人,闻其父为名医,故蕉兄亦能知医云。余与之相交最晚,解放后在平襟亚衡先生座中始相识,时平君以《书法大成》稿本求白为审定者。先是:余久知其为一狂而懒之名士,报刊上亦时见其文字,小品文似专学袁中朗一路者。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
至五六年十月,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他为十委员之一,兼秘书长,闻为文化局科室调充者云云。时二个委员,一刘海粟、贺天健,均旁若无人,白反觉更和气了。但余从不与之多谈多话。及大鸣大放开始,白写了一篇洋洋文章,论书法,竟认为中国无一人懂书法、擅写字(隐隐以他自居为第一),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东乎”。遂被揪了出来,问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先已有刘海粟、张守成等,戴上右派帽子,最后召内兄、钱瘦铁、陆俨少及余四人,劝自戴右派帽子,可以早脱云云。故吾四人同具名请自戴者也。初白与余二人同管资料室,后余至淮南,遂无消息了。及六二年余回院后,白已调去美校为教员或秘书矣。从此不相处一起了。至六六年后,又闻其与余等一样作了牛鬼了。及去岁余回家后,始知白已逝世了。据徐生告余,当其斗争最烈时,白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时犹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
白狂名至大,但余觉得,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馀邪?白书学右军固佳,晚年作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
邓粪翁
邓粪翁钝铁,上海人,以刻印著名,能小楷,亦作诗。陈蒙厂与之少同一业师,最不齿其人,云:先登报报丧,隔三天,又登报粪翁复活了。更名粪翁,即意欲使人引起注意也。
邓生平只拜服一常熟赵古泥石,刻印一以为法,自刻一印曰:“赵门走狗”。印谱曰《三长两短斋印存》,自云:三长,诗、书、刻,两短,不能琴、棋耳。在戊辰、庚午几年,余以吴仲垌兄之介与之相识,登楼欢谈,见卧室一额,曰“厕简楼”。余问何典。曰:马桶豁帚也。及叔师故世后,余治印生涯日盛,曾订润例,速件加十倍。他亦订润,速件草草者,减九倍。见余即若不相识矣。盖同行嫉妒,每每如此也。惟有一事应记之如下:他尝为某寺院写“大雄宝殿”额,寺僧求署钝铁名,不允,仍以粪翁二字署之。胜利后,上海四明公所求画家孔小瑜绘蒋光头长衫坐石上小像一幅,上求粪翁题字,他题了仿伊墨卿体隶书四字曰:“后来其苏”,款署散木敬题。嗣后遂以散木为名了。闻其门人单孝天云:已患肝、胃、肠三癌并发而死于北京矣。他生平最知已友人,厥为白蕉与沈禹钟二人而已,余者都怕其狂而怪,不敢之与亲近了。来楚生治印,似学邓者,但比邓为佳,字亦比邓为雅也。
陈小蝶
陈小蝶蘧,杭州人。其父即“天虚我生”,老蝶也,以无敌牌牙粉、家庭工业社起家,盖暴发户也。其父本自命为词人文学家,小蝶亦颇擅之,但所作诗词,湖帆以其出韵处一一圈出以示人者也。自其父死后,他大权独揽,遂长袖善舞,大造房子,卖买地皮,以度其豪富生活了。一方面大画阔笔山水花卉,与刘海粟、李祖韩等来往,又厕身于书画家之中了。钱瘦铁穷困时尝住其家至久。陆小曼、翁瑞午,亦为其老友,时时过往者也。余即于小曼处与相识者,当时见其身穿纯黑色服装,毛革黑夹袍、黑丝绒帽、黑色帕、黑袜裤,当年只上海捕房中探员“包打听”如此服饰,他乃效之,余殊鄙视之。
某日晚上,瑞午在小曼家中,忽然“云飞”、“祥生”、“黄色”、“利利”以及几个小汽车公司纷纷开至门外云:“叫的车子来了。”瑞午下去说未叫,竟要赔损失费云云。幸瑞午云,要叫只一二辆即可,况吾们自己有车的,何必叫这么多呀。始一一去了。次日小蝶来笑问,车子多伐?瑞午始知其恶作剧也。在杨云史诗集出版后,登报每部十元,小蝶知余与杨亲戚也,嘱借阅一下,余取以示之,隔三月后询其可还否。他云:这种狗屁诗,不通之极,早已撕作碎纸烧烟了(时他亦吸毒)。余云,吾要赔十元了。他云:这种东西可卖钱?放屁,你告诉杨,吾说的。又一次他以电话约余观杨小楼《夜奔》,余与之同进场,只二个位子,他夫妾二人坐了,对余云:对不起忘了定三座,你去罢。余大窘。时湖帆夫妇偕子三人同在,为吴夫人见了之后,即招手命其子让余了(他们母子挤在一起了)。此二事,足可证明此人不但狂,而直是一个妄人也。他只对湖帆、李祖韩二人不敢嬉弄,其他友人无不为其侮骗以为乐事者也。但有二人,为其身旁类于蔑片者(姑隐其名),一,法院书记出身,受其熏陶,居然能画甚佳之山水;二,亦小纨绔子,因久随其旁,亦能写写短文评评书画者,此异数也。
胜利前夕,上海书画家,开展览会之风大盛,他与李祖韩、秦子奇、徐邦达四人合股开“上海画苑”于成都路静安寺路口,专门出租取巨费,张大千三次展览会均其处也。解放前,他即以投机失败了,把所有工业社股票,悉数让给了当时颐中烟公司巨头胡伯翔(后亦为画院画师,牛鬼了),他即携妾去香港台湾了。在香港时闻曾为杜月笙秘书,写了无耻的杜氏自传一厚册。至台湾后,又写了一册什么杂记,内有一则云:“知悉吴湖帆穷困得无以为生活,已返苏州,在路上摆香烟摊,藉以苦度光阴”云云。他这种用心,骗稿费事小,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罪不容杀也。台湾解放后,此人无所逃此罪责矣(该书,有人寄与湖帆亲见之者也)。
徐邦达
徐邦达,荃,浙江海宁人。父名尧臣,乃某国连纳洋行(专收买中国蚕丝者)之买办,一市侩也,暴发之后,附庸风雅,喜遍求当时名书画家作品,以为乐事。邦达,其幼子也,故自小即以东涂西抹,学画为乐。其表兄名孙元良,乃赵门弟子,余师弟也。故以孙之介,始认识之。时邦达只十二岁,一见余即探怀出名刺一纸,视之,徐荃,邦达也。老三老四地与余连连称久仰久仰,余为之竟瞠目不知所对了。余戏询之曰:尊名荃,与邦达,有何关系?他云:我要合黄荃与董邦达为一人呀。余云真乃雄心壮志,可嘉可嘉。但只觉好笑不已耳。
他本无师自修者,十五岁时已居然甚佳矣(他用功是死临硬摹,非任何人可及),十七岁时赠余一帧著色山水(园林景)《安持精舍图》,至今尚存,昨检《急就》残片时,同时取出,今日重观,较之现代自诩大画家之徒,亦无多让也。大约当年他不知从何处临摹而成者也。孙元良死后,他即嘱余先拜赵公为师,因见叔师非山水专家,故又嘱余再介冯超然为师,冯门定例,每年需纳三百元,三年为限,他一算,须九百元,乃中止。遂又托人拜了当时小名家李醉石为师。李以学麓台驰名,教授法最好,邦兄由此得了不少知识。后他常告余云:李氏虽无大名,但教画弟一好老师云云。后再拜吴湖帆为师,一,以自标榜;二,得湖帆指授辨别古画方法。于是大大进步矣。叔师一再向他恭喜即此也。
自其父死后,他亦稍稍买古画收藏,成一小小收藏家了。因此与南浔张葱玉珩成为莫逆之交了。葱玉好嫖,专游舞场(张夫人即名舞女也),邦达亦步亦趋,日与群雌为伍,有一丽者与同居有年,不知何故为湖帆另一学生孙某某所迎归。据云:本来二人公有之物,邦达退股,由孙独营了。吴门弟子无一不知之韵事?邦达面似一木鱼,蒙厂与之亦熟,为之题雅号曰“木鱼头”。在抗战后,他亦只二十余岁小青年也,余每在吴家时时见之,他高据沙发,口含大板烟斗,一面狂吸,一面谈书画,偶一谈及贺天健、冯超然等教学生画法时,即摇头不已曰:贻误后学、贻误后学不已(此四字他口头禅也,无处不用及之)。他走后,湖帆辄笑谓余曰:他正在做“后学”之年,而乃旁若无人,真狂,亦真幼稚,可笑可笑。又:湖帆对任何物都爱惜,一纸之破角,亦必聚而藏之,云可作草稿用。邦达吃板烟不带火柴,时时取吴火柴燃吸,一日,余吃香烟,即就吴榻烟灯上吸之。吴忽拍余肩而云:某某,你好的!你看,吾用火柴之后,梗子终留在牙扦筒中,一再示意邦达可用之。燃后吸之,他,左一根,右一根,取火柴狂吸,未免浪费,只要是必须用的,哪怕送他一大包也可以的呀云云(因记邦达之狂附述湖帆之俭)。在汪逆六十生日时,湖帆自画四画,嘱所有门人合作十二幅山水、花卉翎毛、博古,以取媚祝寿。邦达拒之,且到处扬言,不作汉奸,不附吴党云云。师生关系乃中断了。邦达之名更大著了。所以一解放,四九年秋,郑振铎为北京市文化局长时,招张葱玉任处长,葱玉以邦达为介一同进京了。那日,葱玉请郑晚餐,介见邦达,余亦在座,同座者尚有徐森玉、吴瀛。徐向郑丑诋溥心畲(溥正拟应召进京,故迭以事中伤之),吴与余初见之友也,亦大诋马叔平不止。邦达循循然,居然下属态度矣。后郑氏升副部长后,邦达遂升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了。
他见任何人都狂极,只见余一无狂态,因其子书城十三岁时即拜余为师,毫无报酬,而当时成为余学生中唯一佳才,故有此深交也。六二年余至北京时,途中见之,坚邀至其家中,泡茶请吃,异数也。后余屡得叔羊来书云:吾时访邦史,他从不回访,何故邪?余告以狂人之态耳(他自知沈副委员长不会招待之,故乐得自高身价也)。但去冬叔兄来信云:邦兄六六年后,被遣送江西劳动数年之久,近已回京,变了一个谦谦之士了,亦来谈谈矣。此真党和政府能教育一个狂人而做了新人。可喜之事也。
稚柳对之终不谓然,云:他云生平所钦佩者只一王麓台,太可笑云云。余知之,大约不忘李醉石之教导也。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墒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寓居上海人。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又为诗人,并擅书法,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1980年9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他与许多文人雅士都有深交,如吴湖帆、张大千、溥儒、冯超然、谢稚柳等。
相关文章
- 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4)2017-08-08
- 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3)2017-07-26
- 篆刻—印章知识大全2017-08-08
- 读印之乐:齐白石“见贤思齐”印2017-07-11
- 什么样的印章能拍出天价2017-07-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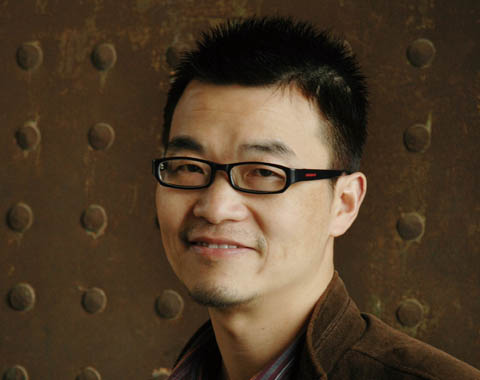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