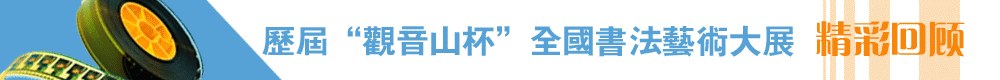七年前,我在江边为公共领域的所谓事功已奋斗了近十年。渐渐,如杜工部“苦被徽官缚,低头愧野人”的书生毛病,便向阴暗角落的霉菌滋生出来。其时,从城里传出消息:巴秋去北京了,地点是荣宝斋画院。这在我,就有了震感。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与我在文联共事,交心多有《离骚》“退将复修吾初服”的意思,较多时间则是“言必行”的临章草,习山水。虽非经美院训育,但丰富的人生历练、良好的美学素养确凿让人看到他明显不属附庸风雅一类。他上手太快了,在本邑、以至去省美术馆举办“个展”,都曾因不明方向的非议而心生纠结;他起步太高了,山水一开始就学黄宾虹。需知那“杂乱”里的内在结构、衰年变法的规律,师黄,是何等易学难工?那时所画,大约就是古人闲章印文的“聊传形迹”吧。想到黄宾虹成功的曲折过程就心有存疑:难道追慕大师必定要沿一条直线或者非得背井离乡么?固然我十分赞同汪曾祺先生鼓励青年人“走出深街里巷”一定要到外面去的真理性见解。可是巴秋的“北上”毕竟是在年近六旬?消息是可靠的,他的出发是毅然决然的。就这样,这个“荷戟楼”(因鲁迅诗而得其斋号)里独彷徨的一“卒”,将昔日那些曾经直面或侧面于他的妄自尊大的鄙夷、尖刻得毫无修养的冷嘲、缺少起码宽容和发展眼光的品头论足,以及小城虚拟的名利场、没有章法的倾扎……,统统抛在身后了。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喜怒于色的人在有着艺术宗教气氛的荣宝斋,怎样一笔一划地从头再来?他将以何种姿态伏案来适应或迎合那庙堂之气?
结果是,巴秋一“伏”就是八载多,将近一个“抗战”的时间。荣宝斋,巴秋在“扫地焚香”中虔诚地遁入老圃师门,将“遂其初志”的难得机缘化为来者可追的饮墨豪吐;在“工者苦心”的领悟中,从画院走向山川,又从外象走向内省。他在同学之间,大约一时还难改直抒胸意的旧习而常有雄辩。然而,在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下,健康的明辨绘事精微的过程,已将昔日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和尚缺实力的自信荡涤成觉今是而昨非的提升。同学一拨拨来了,又一拨拨走了。巴秋这个年纪明显偏大的老学生却未走。老圃先生的厚道以及之于巴秋亦师亦友的关系,客观上使巴秋获得“秋月春风等闲度”的颇适艺术成长的环境。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但恰恰是这个“慢”的过程,他的山水开始“意与古会”,甚至有些元人的笔意。一番花事又经年,他首先进入“花事”的梅,让人欣然于暗香浮动了。从来“问梅消息”,乃是问道。巴秋兼工带写的梅朵、枝干,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气。那些古朴的瓦当和大胆留白,简约中传递出多少人间消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散文中以然认识到“梅”在自然之中、观“梅”需距离以及世俗眼光的误读。这是巴秋进京最初几年画作给我的印象。我以为,笔墨训练与视野的开阔互利互惠于素宣之上,正是巴秋日渐有功的因果。对巴秋而言,“京飘”的身份近乎流浪,更加执着于中国画的文化血脉,则是归属。而中国画文脉的探寻在笔下真正成为某种修为,则是老圃团队(北禅写真院)一次次革命性“写真”。巴秋随老甫走向山区、平原,走向只要有适合的土壤就能长出的蔬菜、瓜果,走向农耕文化的朴素记忆……,并且把他一口口品味、抚摸的体验,在八年后的今天倾诉于不同城市的美术殿堂,让熟悉、不熟悉,或曾经熟悉而又陌生了的眼睛一同分享他的快乐和得意。
巴秋的蔬果系列,审美取向与师承显然来自老圃,甚至题画款字亦酷似。然而,亦步亦趋,首先是建立在将老圃作为精神领袖这一基础上的。在当代中国画坛,老圃在某些方面颇似唐代的王维,如“居家蔬食,不茹荤血……不衣文彩……”,“斋中无所有,唯茶铛”。据说老圃亦深谙茶道,且用清泉入壶。茶之道不外乎“凡、素、静”,而佛学中的“戒、定、慧”同是以静为基。这又与自许“前身应画师”的王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一脉相承。如果说,老圃先生“愿以园中鲜翠之物为一生所研绘”,是从有着高度象征的“野茴香花”(奶奶)而为最初情感动因,那么,巴秋追随圃师能否深切理解从绚烂中复归之平淡呢?这关键,老圃从巴秋的“痴”和由“痴”带来的“毫无世俗之气”的蔬果中已流露出“惊喜”,确认这是佛家的“平常心”。这个温暖而知性的褒奖,无疑是对巴秋创作某种方向性的肯定和鼓舞。由“平常心”也引发了我对“写真”或工笔写意性的思考。当前中国画工笔花鸟的情状,除少数成功者外,实在可归为富饶的贫困。其语言形式的概念化、技法传承上的所谓勾、染、且不论,更尴尬的还在于:既无法与西洋画的色彩丰富、微妙比肩,又没有宋院体画的雍容,精神、品格(我个人从赵佶的作品甚至能看到“普世”的光芒)。多年前我在已故的秦克诚先生(陈之佛弟子)家看到50年代初陈之佛赠他的一帧小品“一枝春”,既有宋人笔法又有浮世绘元素的工笔,确是今日稀缺之物。关于浮世绘,如同我们对日本研究的其它方面一样——常常把地理上的临近、人种上的接近,误解为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近似。其实,如同日语的开放度一样,浮世绘对西方绘画的吸纳也是空前的。虽然我们要确认“现代性就是深刻的个人性”这个观点一时还有难度,但现代一词,确实标识了所有时代中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只有在这个自我更新中,才能形成活的传统。在讨论工笔的写意性与中国画特有视觉方式的关系时,我注意到老圃将视觉方式与心理运思方式合称为视觉心理方式,并苦寻其切入点。这本身便显出超然与高迈。出走同时是返回的过程,是精神的自我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圃基于中国画理的开创性工作,虽不能说力挽工笔花鸟画的狂澜,但确有坐标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太需要如宋元之际的赵孟頫这样天才式人物,不但需要有悟入绘画文脉的天资,更需要有突入绘画原态的禀赋。悠悠岁月,我们始终纠缠于“坐实于形”或“为形所累”;我们总是小看苏轼、米芾的不善画,而疏忽他们在绘画的“道”“器”关系认识上的高度一致。老圃对中国画蔬果的新“写真”贡献,巴秋不二法门的师承,带来工笔花鸟画坛全新的气象,耐人寻味。
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写真和写实是绝然不同的。巴秋们的写真,除了“身行万里半天下”的境界提升,更重要的是“学养”和中国画“私人状态”的重塑。学养的大敌是对象的固式化。《宣和画谱》大约已有蔬菜门类,虽有知性评说,却以开始将对象固式化了。到了由“四王”整理出来的《芥子园画传》,基本已将图式与学养之间的血脉割断了。图式的普泛是大众化的前提,这就成了近代中国画坛的“卡拉OK”。民间就是旧时所谓“家家子久,人人石谷”。到了“家家”与“人人”,中国画的“私人状态”――笔墨与心性、作者、作品与日常生活的合二为一,渐渐就被消弥。回头再看齐白石的“蔬笋气”,与其说是乡土情节,真不如说是“学养”与“私人状态”的高度融合而让人感慨良多。写真,面对大千世界蔬果的写真,最要紧的可能就是“学养”和某种“私人状态”。而它的前提,恰恰是回归了的一颗“素心”。
巴秋已然获得的“素心”(或曰“平常心”),应该是“洗”出来的。他在《怀念冬日的阳光》里“洗”,在《湖畔洗心》,在《走进小巷的暮雨》中还是“洗”。他像一个半路出家的信徒在北禅写真院里紧随老圃这个大德高僧,必是抱了洗心革面的决心。他由“心性”到眼中的“心相”直至“心法”,已不是空穴来风,乃是自然的递进与出神入化。关于通过“写真”“找回艺术本心”,巴秋在晚报上的著文,已作了艺术宣言式的解读。而关于“写真”话题的另一种生活的表达,他则在另文《细节的快乐》里象布道者一般向我们传达出关于幸福的哲思。“始知真放在精微”,现在,他因描写那些蔬果上纤毫毕现的细节而“对美好事物敏感了”。他因“一日不可无此君”的蔬果,“对幸福的追求变得简单起来”。在这并非疾风暴雨而是类似暮鼓晨钟般的时光之水的“洗”汰之后,他说:他的心“变得清净而柔软了”。心房的柔软,便是“道”的入驻。
予不敏,学书多年,却无寸进,遑论读画,故多在门外,月旦人物更非所长。只是每见友人进步,内心总有欢欣。旧雨新识,率尔成文,权作从巴秋作品前匆匆走过。
姚舍尘,著名作家
相关文章
- 师从任颐,和吴昌硕亦师亦友,蒋介石赞:清标亮节2017-10-27
- 知道每天电脑输入的行楷字体是谁写的吗?2017-08-10
- 石涛致八大山人书: 哥们来张画儿2017-08-08
- 徐悲鸿画猪:气韵生动,憨态可掬2017-07-31
- 一树梅花一年翁2017-07-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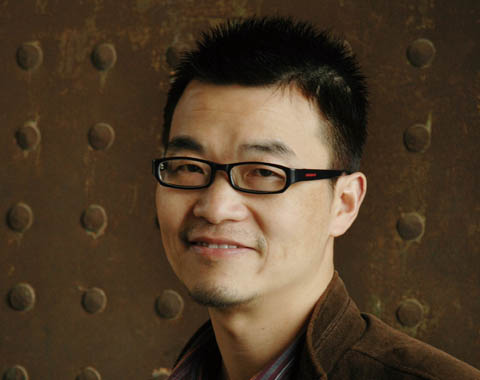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