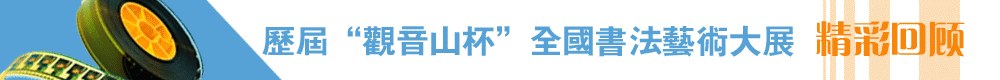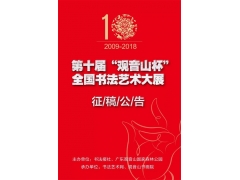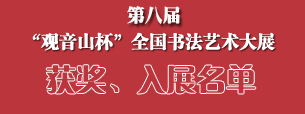没信的时候,信成为时尚
随便一问,周围拿笔写家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曾在MSN上郑重地对多年好友说:“我准备给你写封信。”朋友说:“给我写信?出什么事了你?直接电话说。”
其实,出事了的,是我们自己快餐化的情感。
有信的时候,信很重要
有人说,书信大体上算是一种情感大于载体的东西。这话是对的。我对朋友说,我没事,我只是想静下心来用真正的墨水笔表达一次。她不置可否:“哦,期待但稍显文艺。”“文艺”是“矫情”的客气说法。而就在不远的过去,写信是绝不会被戴上矫情这个帽子的,眼下,它却真的成了需要经常拿出来晒的记忆。
教钢琴的周老师是有些怀旧情调的,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总喜欢把收藏的书信拿到院子里晒晒,顺便在暖阳下翻看几封。然而这个春天,他发现其中一些已经发霉破损了,还有些虫蛀的痕迹,甚至在箱子的边缘有疑似老鼠的牙印。一旁爱人说,“扔了吧,这都多少年啦!”周老师想想,又想想,还是决定收起来。他的收藏里,有多年前儿女的、朋友的书信,更大量的是夫妻俩年轻时的通信。
王老快八十了,他的手头有十几封初恋女友的情书。虽只是用订书机简单订了,纯蓝墨水的钢笔字迹也已逐渐湮没在发黄的信纸中,但每每捧起这些信,他依然流泪:“她不在了。去世多年了。可每次看到这些,就想起在车间外夹竹桃下偷瞄她又害怕被发现而假装路过的情境。后来,我们偷偷通过几封信,彼此确定了心意。”只可惜由于成分原因,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这几封信,成就了一个人一辈子的爱情想象。美好,也苦涩。
有信的时候,信很重要。
在机关工作的林女士对信有一段深刻的记忆:“那时候的信,作用大到你无法想象。”
村里有个强悍的姑娘叫小芳,当嫁之年媒人给介绍了一位解放军,不曾想解放军回来一看不大满意,写了封很客气的信,大意是“可以做朋友”的婉拒。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芳“在一个夕阳格外好的下午叫住了放学回家正上初二的我,说你来帮我看看这到底是啥意思,这朋友处还是不处呢?你帮我给他回封信吧。”于是在那个晚霞满天的下午,初二学生小林动用了自己情窦初开的所有想象,给从未谋面的解放军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这年冬天,解放军就回来和小芳结了婚。摆桌请酒时,小芳把解放军拉到小林面前:“她是我们的红娘,那封信就是她代我写的。”解放军文绉绉地说:“哦,写得真好,文若其人,人若其文。”
这件很容易被小说家看重的故事,其实在当时并不鲜见。
张女士当知青时的爱情就是靠信件维持着。丈夫上大学,自己还在农村教书。“两人约定每个星期三都写信。有一次没来得及写,就接连收到他两封,第一封写今天没收到信,出什么事了?第二封是第二天写的,写今天收着信了,放心了。”
有一段时间,张女士回娘家住,丈夫把信寄到了丈人家,竟然在小村里引起了大风波。村里人小声议论:肯定是跟丈人说要和他女儿离婚,人家现在是大学生了!丈人瞒着女儿把信封口裁开,发现“情况好得很”,又原封贴回去。后来老丈人在村里得意洋洋地走了一圈,第二天村里人碰面就说:你们别嚼了,人家说的是放风筝的事。
等待,是书信的主题词
等待,在书信来往中绝对是关键词。
说到等待信件的痛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最有感触。朱先生已奔不惑,然而对初恋女友的决绝至今无法释怀。这个文艺男青年上大学后每次给远在北京的女友写信都要附上N首诗歌,可是书信一去便杳如黄鹤,他每天辗转反侧,情绪低落得让宿舍其他七个哥们看不下去。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寄信的时候八个小伙儿站在邮筒前一起高喊:“某某,快回信!”后来真回了,却是一捆退信,这不着一字的信带来的伤害,朱先生至今无法承受。
等待通常需要一个人来解围。在普遍的记忆中,邮差先生是绿色的,是希望的色彩。张女士在乡村教书时,每个星期三都盼着邮递员。“那时候全乡就两个邮递员,负责我们这几个村的叫赵雪成。我在班上教课,眼看着一个绿色的人骑着一辆绿色的车从窗前经过,心就开始跳:今天有我的信吗?好容易盼到下课钟,冲进办公室,总有一封信方方正正地放在桌子中间,两本书压着信角。”4年里,赵雪成在张女士心中如亲人一般,“国字脸,嘴角上翘,什么时候都像在冲你笑,老远他就‘嘀铃铃’跟你打招呼,一边还拖长音喊,小张……信!”
贾沛华在扬州做过多年的邮政分局局长,对“等待”与“书信”,别有一番话语——
邮政业发达的时候,家家户户都靠信维系着相隔两地的亲人的联系。谁家出了事,谁家寄了钱,好事坏事,邮递员心里都有八成数,比现在的片警还熟悉情况。那时候,家家都拿邮递员当亲人。邮递员的自行车一响,家家都盼着有自家的信。等寄钱的人家,早早拿了章在门口等着;要寄信的人家,拿了信件等他来收。那时候邮递员有步班,背一个邮包靠两条腿走街串巷,穿过一户人家,经后门又到下一户人家,熟络得很。后来有了永久28大杠(一种自行车型号),技术练兵的时候,专门有一项就是自行车技巧。现在基本是电动摩托了。不过无论交通方式怎么变化,家信,邮递员是一定要背在身上送的,“家书抵万金”嘛。
没信的时候,信成了时尚
如今,人们习惯了电话,习惯了网络。短信、QQ、MSN、微博,以及一切新鲜的聊天工具,似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远隔重洋也只需闪屏一下,想表达或想怎样表达,分分秒秒便能搞定。有人批评现代人的感情太过潦草、不耐咀嚼,虽有些武断,但那种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感觉确实已成过往。
寄包裹也不再猴年马月地等了。现在有个快速成长中的行业——快递。快递只要拿出职业精神,国内再远也能三四天到。不过,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创意的脑袋瓜,突然有一天,出现了和快递较劲的慢递,并顽强地成了一种小众的时尚,好歹拖住了书信凋落的尾巴。
扬州小店“蘑菇杂货店”有一面慢递墙。那墙上下12层,一层5格,6天为一格,来的慢递信按照日期分格放着。店主人准备了各式各样的个性邮票,按照客人要求的时间,去邮局把这些信寄出去。“绝大多数都是明信片,有寄给自己的,有寄给别人的。期限是10年。即使十年内我不做这个店了,我也会承诺把这些信寄出去。然而,这些承诺也只停留在口头上,彼此之间没有法律约束。圣诞节前,店主特意买了明信片寄到全国40个地方,“目的是问候老朋友,再就是考察全国各地邮政投递情况。慢递基本属于一种时尚行为吧,用上海人说法,有点‘腔调’。”
当写信被看成一种“腔调”,这就格外证明它真的成了人们可以放心缅怀的历史。
贾沛华这几年就恢复了这种腔调。她一直有着给早年的舞蹈教练“过年寄张明信片”的习惯,上面无外乎是身体健康、万事遂心的客套祝福。老教练80岁后,终于提出来:“不要寄明信片,给我写信”,并给昔日弟子做了“示范”。贾沛华说,“老师每次都写满满五六页纸,知道我也老了,经常抄些杂志上的养生方法给我。一字一句,全是手写的。从来不简单地复印。我现在也不敢怠慢,每次回信也是满满地写,写过去共同的记忆,写自己现在的生活,彼此间的感情似乎越来越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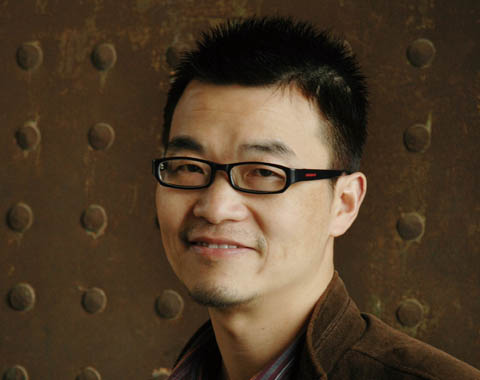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