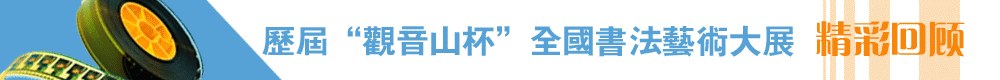我曾经与他在仙游的深山中度过四天三夜,在寒冷的山野间看着他凝神屏息,描绘寒冬的冷云与冻雨。我拍下了他挥毫泼墨的瞬间,也拍下了他那冻得通红的脸颊和鼻子。
那几天,我们一路向西,去了西宛的凤顶、凤山、度下、墓前、溪尾、溪头,还穿越险峻的盘山公路来到与永春、德化、永泰交界的东湖和白岩。他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天赋,搬了张可折叠的帆布小椅在山沟沟里任选一个角落随便一坐,就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角度,捕捉到每个场景最为奇特的品质。
他开始一笔一划描绘它们,先是村道,房舍,然后是村道和房舍之间的树木、篱笆、小桥、流水、农田、牛羊和劳作的人们。当然,还有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峦,迷迷蒙蒙的雾气以及他所能感受到的一切。
在他看似轻松随意的构图中,充满平衡与协调,营造出迷人独特的空间感。只要我们留心察看,便会发现他的每一幅作品以及同一幅作品中的各部分之间拥有一种相依为命的紧密关系。他仿佛对眼前的一切了如指掌,保持着过人的敏锐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往往通过寥寥几笔就得以确立并呈现。
待到他放下画笔,停止工作,他会拿起画板端详自己刚刚完成的劳动成果。这时他也许会在画面中看到属于艺术的而非大自然本身固有的美感与神秘,看到自己心灵深处不足为外人道的某种情感和意识。眼前的这幅刚刚还是白纸一张的纸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是大自然与画家联姻的产物,是两者偶然间的一次亲密接触而孕育的独特生命。就像所有刚刚诞生的生命一样,它有着令人惊讶的新颖。他心满意足又心平气和地打量着自己的作品,就像母亲打量自己刚刚出生的婴孩。
一幅画接着一幅画就这样诞生了。它们各不相同又似曾相识,是同一母体的不同孩子,同一物体的不同侧面,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管怎样,它们都拥有一种同样亲切、美好的品质,拥有一颗同样朴素、诚实的灵魂。站在这些画作前,如果我们有一颗平常心的话,就会发现并感受到画家带给我们的素朴之美。它们存在着,并不高深,却也不容低估。
这就是国雄的画作。他只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眼前的山山水水。他自信坚定地跟着自己的视觉走,他看到了那些常人看到的东西,也看到了另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总是看不够,画也画不够。谁知道他接下来要画什么,将来又会画出什么样的名堂来呢。
一、关于梦想
麦冬:青年美展揭晓那个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徐国雄:我在画画,也是每天既定习惯的时间点的工作,已经习惯了。古人云: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如果一天不画就觉得缺少些什么。很多人讲画画需要灵感,但灵感从哪里来?画画需要下大功夫而又有悟性,我觉得灵感是建立在画家用千笔万笔的练习基础上才能得来的,这跟科学家搞科学研究一样,没有精确的千算万试哪里有科研成果,这两者道理都是相同的。
麦冬:还记得站在一号展厅里的情景吗?
徐国雄:二十年了,梦想终于实现!终于成真!终于在一号展厅展出!
麦冬: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总算是个画家了,而且是个不错的画家了?
徐国雄:当时我倒想,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画家得去画画,去体会,去体验生活。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麦冬: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画家?
徐国雄:没有真正去想,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只是喜欢画画,做画家只是一辈子的工作而已。
麦冬:还记得你画的第一张画吗?
徐国雄:记得,那是1986年2月底的一天,我在帮亲戚家看工地时借了一本当时只有初三才有的美术书,临摹了一张元代倪瓒的“六君子图”,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张画。当时只是一个人在那里没事干,只有看点连环画,武打小说来消遣时光,然后就是用毛笔来涂鸦,连素描是什么东东都不懂。
麦冬:你家靠溪边吗?可以看见壶公山吧?
徐国雄:是的,我小时候常去木兰溪边,听溪水的声音,抬头看南边的壶公山,看山顶云彩的变幻。
麦冬:你总是说,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徐国雄: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在很小的时候,每逢周末及假期我就随父母亲一起去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劳作,一直到天黑。
麦冬:为什么辍学?
徐国雄:因为家里穷,书又念得一般,过完虎年元宵节(1986年)就不去念初二下学期的书了,那年正好我表哥家要盖新房子,在筱塘村那里的山窝边弄了块地盖房(就是在你们报社的位置,当时那个地方四周都是麦田、甘蔗林,还有几座孤坟伴着),呵呵,按现在的说法,我当时还是个童工呢!
麦冬:你觉得农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徐国雄:勤快、吃苦、耐劳、乐观、豁达且坚忍不拔。
麦冬:农民和艺术家是一种什么关系?
徐国雄: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所不同的是,他们是一草一木的去耕种,而我则是一笔一划的在耕耘。一亩三分地里同样浸透了我的无数汗水和泪水,也同样洋溢着无数丰收的喜悦和欢欣。
麦冬:所以你一口气就画了492幅?
徐国雄:确实很难,因为完全是微型山水画,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方寸之间,群山、流水、花卉、林木、田野、农舍、人物、书法等什么都有。从构思布局、运笔设色到浓淡干湿、阴阳虚实等,对传统的技法都要有所突破和创新。
麦冬:因为是“农民”,所以你似乎什么时候都有状态,对工作环境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我去过你的画室,也很简朴。
徐国雄:对工作环境还真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能有适合画画的环境,站着,立着都行。
二、关于北京
麦冬:张仁艺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徐国雄: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法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对他艺术生涯终生受用的两样东西:一是立足于传统;二是不停地写生。这两点我受益匪浅。
麦冬:你一直跟张仁芝先生保持联系吗?
徐国雄:在创作上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法,还是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困惑的事情,常常打电话向他请教,都能得到一一的解答。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麦冬:你说师兄段铁对你的成长之路起了很大的帮助。他是怎么引导及支持的?
徐国雄:“你就代师授徒吧!”老师的一句话,我段铁师兄没有二话就负起教我这徒弟的责任。从一棵树、一块石头如何下笔起及到最后整个画面的构成,他都要求的非常严谨、严格。他告诫我:画画没有捷径,也无止境,基本功一定要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要急着什么时候能成为画家,要学会鸡蛋里挑骨头,从每张作品里看到不足的地方,然后怎样处理会更好。他还鞭策我做人要实在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点小成绩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些年要是没有段老师的精心指点和教诲,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这一点点小成就。他是我师兄,他更是我的老师!他待我像亲兄弟般,挂念我,帮助我。我很没礼貌,老是称他师兄。
麦冬:当年在北京还办了次展览?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在什么地方展出?
徐国雄:那是1991年4月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办的三人画展“于文治(释妙虚)、石峰、徐国雄画展”。
麦冬:都展出了些什么作品?反响怎样?
徐国雄:展出了一些那时画的山水作品,主要以黄宾虹及黄秋园两位前辈大师的风格作品。那时也不懂,谈不上反响啥样,只感觉很激动又很渺小。
麦冬:北京回来之后做了些什么?
徐国雄:卖画糊口,但学的东西跟市场不接轨,真正体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穷画家”生活。
麦冬:回来后也办了个画展?
徐国雄:93年12月份在莆田古谯楼办了个展,当时只有22岁,当时只是想把在北京所学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三、关于写生
麦冬:为何选择家乡的这些小山小水?
徐国雄:因为家乡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纯朴、勤劳与善良的乡民,小桥流水、山泉飞瀑、竹林灵石、幽谷碧潭等等,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有那种熟悉的泥土味,热情好客而又善良纯朴的人们,一切都那么亲切,让我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犹豫的去表现、去讴歌他!
麦冬:最早一回是什么时候?
徐国雄:第一次去了度尾的屏山和苦竹,是雇了一部出租车去的,画了两张梯田速写,那时还不懂用毛笔在宣纸上直接对景写生,那年应该是07年的春天。
麦冬:还没买车吧?
徐国雄:那时买了一部踏板摩托车,骑着它三天两头的往山里跑,有点像古代骑士的样子。
麦冬:怎么想到画这些小画的?
徐国雄:小画作品尺幅虽然微小,但寓意深远。它能透射和印证一个画家的功力、灵性、素养和才气,小中见大是中国画“天人合一”的追求,可谓“咫尺之内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写大千世界”。美术创作里有两个极端最难:一是大作品按小作品来画很难,二是画面结构复杂的尺幅极小但内容丰富的小作品最难画(俗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麦冬:当时没有想过会把它画成一个系列吧?
徐国雄:当时是没有想过把它画成一个系列,只是画几张作为画稿当参考资料,2010年9月份的时候拿到张老师那里请老师指点时,张老师说有机会可以画一个系列的作品,然后组成一张有意思的作品出来。
麦冬:如何观察自然?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地方的特质?
徐国雄:我的写生,重视情景交融的直接感受。直接写生得来的东西,即使很粗糙,不成熟,但是富有生气,清新而有活力。写生过程中一定要有生活气息,画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有现场感,最少要保留百分之七十的现场感。
麦冬:你觉得画画苦吗?寒冬腊月待在山里,冻得浑身发抖。
徐国雄:不苦。很快乐。如鱼得水。感觉就像战士上了战场一样。
麦冬:你在北京有工作室,却又一次次回老家,一次次地往山里跑,始终乐此不彼,与大都市相比,你似乎更喜欢待在山里。
徐国雄:是的,我热爱大自然,尊重大自然给予我的一切感受。在绘画过程中,生活的感受和艺术技巧的锻炼都是大自然给予我的恩惠。当我迷茫时、当我困惑时、当我苦闷时,我就走村串户、游历家乡的山山水水。以一个画家自己的眼睛去体察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大地上的勤劳而善良的人们。大自然给我带来无比的力量和欢乐,给我带来情感的抒发,给我启迪和联想,给我无尽的灵感。
麦冬:最先吸引你的是光线、色彩、造型,还是整体的空间感?或者是一种特殊的氛围?
徐国雄:最先吸引我的是一种人文情调,更能唤起我对岁月沧桑的回忆,还有时代的烙印。
麦冬:你享受山里的安静吗?孤独吗?
徐国雄:面对大自然。渴了就喝喝水,困了就睡睡觉,何其自在。你说我会孤独吗?
麦冬:画上的一些题字很有意思,特别生动,亲切,把人带进画中,带进你创作时那种氛围,能感觉到你当时心态。比如,“此地有弯路”,“去某某路上有此佳景”等,很朴实感人。
徐国雄:我只是想告诫自己艺术这条路不能急功近利,前面的路很弯很曲,又不平坦,要慢走,一步一个脚印来。
麦冬:你觉得这几年写生给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徐国雄:旅行写生,无非是要自在和快乐,和在城市里高楼间的暄闹、烦躁、急切、匆忙的生活不一样,行游山水之间,看看与自然乡土所牵连的乡愁,看看生活在自然山水里的中国农民的智慧,获得一种平和静穆的从容,这也许是我在写生中最大的收获。
四、关于乡土
麦冬:吸引你的除了风景还有什么?
徐国雄:首先是风景,但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人文积淀。像西宛乡东湖村,你了解一下,就会知道它有不平凡的历史。1944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派遣饶云山、祝增华等率领武工队进入仙游县凤山乡东湖村先行建立革命据点。同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及闽中特委机关进驻该村,领导全省及闽中地区抗日斗争,遗址为一清末兴建民房。
麦冬:在山里写生,更加打动你的是自然景物还是当地的人文景观?
徐国雄:我们闽中的这片小山水,虽然没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那样深沉和厚重,但它除了同样记载着历史外,更多了几分鲜活,几分亲切。因为它是我们的故乡。这些村庄尽管有些荒凉甚至破败,但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父老乡亲们一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像翁老师说的那样,在那一个个偏僻的山村里,那些荷锄劳作的老农,或是洗衣的村妇,都透显着一种美,一种劳动者所特有的美。甚至于那些小鸡小狗也传递出一种让人觉得无比亲切的乡土情感,它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这里又很安静,可以自由自在的思考,也正是这种情感让我一次次往山里跑,一次次把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描绘下来。我真担心有一天这一切突然消失,而且,这还是一种必然。我每回进山,总会发现某些风景消失不见了。当然,我还是乐观的。我想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也是一种社会规律吧。
麦冬:你的这种情感并不是一开始就展现出来?
徐国雄:从小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愿望、一直有这个冲动:把我身边这些熟悉可亲的父老乡亲,这些最可爱的人画出来,把这片生我、养我的美丽家园画出来。我要尽情地赞美!尽情地歌颂!
麦冬:中国画的传统追求一般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却完全进入了乡村生活。我觉得翁老师对你的评价非常到位。他最为看重的是你对人的关怀。他认为你的画画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层面,更重要的是你所表现的、所透露出的还有一种爱,一份深挚的爱,对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这片沃土上的勤劳而善良的父老乡亲的爱。确实,与对山水的关怀相比,这种关怀更加动人。
徐国雄:在山里写生,无论是荷锄劳作的老农,或是清溪漂洗的村妇,都透显着一种美,一种劳动者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最质朴的美,是一种最值得尊敬、最值得赞美和讴歌的美!那里的小景是那样的美丽,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随便坐在哪里都可以画出一张张充满诗请画意的作品来。夕阳西下,独坐路边,看流水潺潺,思绪飘得很远很远。确实,在山里写生感动我的不仅仅是山里的自然美景,我深切感受到那一个个默默无闻、不辞辛苦、勤奋劳作的父老乡亲,那才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人!
五、关于风格
麦冬:张仁芝先生说你这几年有了质的飞跃,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这种突变是怎么来的?
徐国雄:老师教诲我:读懂生活与传统两本书,静下心来,坚持不懈深入观察体验自然界的规律,探索宇宙万物的神韵,又不断深入揣摩研究传统精华,在艺术创作的崎岖山路上不惧艰难地攀登。相信你自己是一颗珍珠,总会在亿万粒米中闪光的,找到你的前进的路。我正是牢记老师的这段教诲,牢记心中,才有了今天的艺术形式。
麦冬:成功艺术家的共同点就是找到自我,你找到了吗?
徐国雄:艺术创作是一种文化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与宣泄。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态度、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世界的认识,总是会通过其作品或多或少显示出来。
麦冬:山水画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不再故作高深或者故弄玄虚。翁老师对此评价很高,他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觉得你的田园山水画所表现出的内涵与创作情感,与古人有着某种精神的疏离,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山水画。你怎么看待他的评价?
徐国雄:翁老师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觉得很惭愧!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做好。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
麦冬:你怎么看待传统?山水画传统上是文人寄情山水自我放逐之地。他们把内心逃逸到那个萧瑟荒寒宁静淡远的世界里。你觉得这种精神现在还有吗?传统还回得去吗?
徐国雄:我觉得自从传统山水画赖以生存的基础——乡土中国的日益瓦解和文人政治所配生的仕大夫精神的式微湮灭,山水画完全回到传统已成空想。
麦冬:我感觉到你的作品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客观世界,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复制。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但我又说不清这差别是什么。看了翁老师评论清楚了不少。他说,你的写生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景写生,也不是“以意为主”。你的许多作品都保持了新鲜的第一感觉,并又有所升华,有所幻化。因而境象情调不同于古人,亦有别于同时代的画家。
徐国雄:艺术创作是一种高度的个体精神劳动,因其精神性而应该为之提供一个相对开阔的天地,因其个体性而应该使自己的创作务求另辟蹊径。
麦冬:你的作品总是传递出一种清晰、丰富、和谐的韵律。这韵律灵活多变,充满活力,给人极其强烈美好的审美情感。你在创作时,感受到这种韵律了吗?
徐国雄:是的!
麦冬:绘画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但我在欣赏你的作品时却老是仿佛听到风吹草动,鸡鸣狗吠的声音。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
徐国雄:写生记录的作品不会太完整,但生动、鲜活、单纯、朴实无华,点点滴滴散落在画面上,有意无意间写出来的真实,能够给人广阔的想像空间,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你不花更多的时间去读懂自然中的一草一木,就不会把瞬间的情感留在永恒。
麦冬:我觉得你的画面给人总体的印象是和谐。你在简繁,明暗,远近,深浅,浓淡,枯润,冷暖,甚至动静快慢之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平衡。这是你有意的追求吗?
徐国雄:我想在画面中呈现出一种统一性,其实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每个乡村都有固有的节奏感和淳朴天然的生命气息,每一片叶子、山峦、村舍、篱笆、狗和女人都有它的关联感和节奏感,画家要做的是把握并激活它,把它呈现为一种生机勃勃的画面。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就不得不留心每一个局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给所有的存在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关注并描绘。
麦冬:同一题材几百幅画让人觉得不重复,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徐国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同样也没一个乡村与另一个乡村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同一个乡村,它的春夏秋冬、昼夜晨昏也是不一样的。而且,画家的心灵也是瞬息万变的,此刻眼中的山水给你的感觉也许换了种心情去看感受就不一样了。大自然无比复杂,丰富,再说笔墨本身也是千变万化的。
麦冬:谈论中国画跟谈论中国哲学一样,很容易滑入虚空。但是你的画不一样,你的笔下坦坦荡荡地充满了一种人间烟火的气息。鸡犬之声相闻,牛羊田间漫步。你不禅亦不道,要说的话倒有点儒家的世俗情怀和中庸之道。要说禅的话也是一种劈柴担水的禅,一种时时勤拂拭的禅。
徐国雄:“禅”,作为一种宗教,其宗旨是出世的。但文艺作品中所谓的“禅”,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机锋,或者说是对于人生哲理的某种契合,这需要很高的智慧、悟性与深厚的学养。我们要多参禅,少说禅。一说,就禅意去。
六、关于未来
麦冬:除了对题材的选择外,在艺术上你比较看重什么?
徐国雄:情感。
麦冬:你怎么看待你目前的创作状态?
徐国雄:我的许多作品是逼出来的,一方面是自己逼自己,一方面是别人逼我。一个画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理性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心里有什么都会从笔端流淌出来,当然,生活本身并不是艺术。要把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推进到艺术的境地,而不是停留在忠实的传达和复制。这就要求创作时既要投入思想感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画进去,又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主观上的情感参与和意境的深化是艺术的灵魂之所在。只有通过画家特有的眼光去审视、综合、提升,才能表现出既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绘画作品,这才是创造。
麦冬:有人说“吾土吾民”不可重复,不可复制,但你偏偏画了又画,意犹未尽,是不是觉得还没画完这片山水?
徐国雄:我觉得没画完还有往下画的空间。当然我也想有个突破吧。
麦冬:透露一下你的下一个系列会是什么?
徐国雄:我想用8到10年的时间去寻找福建最美丽的乡村,把它写、
画出来,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把它们记录下来,用最纯朴的艺术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
麦冬:最后谈谈你的梦想。有没有想象过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徐国雄:平平淡淡才是真。当画家是小时候的一个梦,当了画家知道身上的责任和自身先天的不足,知道自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坚持!
相关文章
- 师从任颐,和吴昌硕亦师亦友,蒋介石赞:清标亮节2017-10-27
- 知道每天电脑输入的行楷字体是谁写的吗?2017-08-10
- 石涛致八大山人书: 哥们来张画儿2017-08-08
- 徐悲鸿画猪:气韵生动,憨态可掬2017-07-31
- 一树梅花一年翁2017-07-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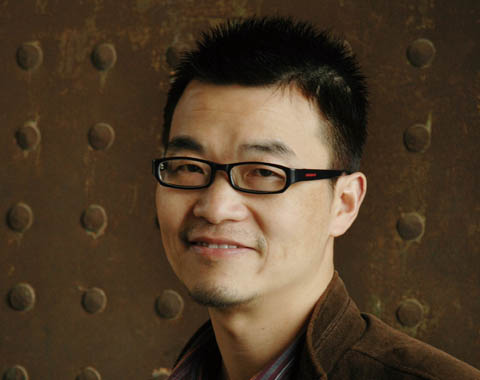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