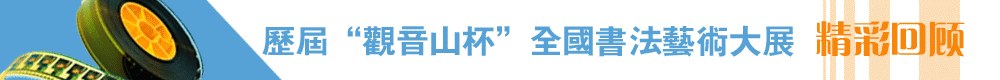一位精通东洋木雕的雕塑家在谈及齐白石时说自己没学过国画,对齐白石的绘画好到何种程度感受不深;但看了齐白石早年的木雕,他认为,若将齐白石在木雕上的天分移诸绘画,也必能成就一代大家。只怪当时没有“工艺大师”的称号,靠技术活儿吃饭的劳动往往被视为贱业。否则,齐白石也不一定会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更易博得社会地位的文人画领域了。
齐白石从民间艺人向文人画家的转型相当彻底。文人画所要求的诗、书、画、印他全都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且有大成的表现。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模仿文人声口的篇什,但这并不是他的本色。他的本色诗可以“质朴清新”四字当之。他的老师王湘绮曾评他的诗是“薛蟠体”。这个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诗作口语化、通俗化的审美倾向。他的诗作中不乏像“打鱼晒网,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之类的俗句、俚语。而此种描写农家日常生活的俗语是不能跻身文人诗学的大雅之堂的,因而其遭到恶评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常以这种带有“打油”性质的韵语配以鲜活生动的画面,令观者莞尔之余,往往能够一见成诵,过目不忘。他的诗和他的画是一体的,都是源于一个农民对自家经历的真实写照。这份感受与文人诗学营造出来的桃花源式的田园风光本就有着质的区别,故其呈现的方式也就不免大异其趣了。他既画梅兰竹菊这些典型的文人画题材,也在鱼鳖虾蟹等不大受到关注的“偏门”上做足了功夫。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犁箩锄耙、蟑螂蝼蛄等题材也都被他一一搜罗入画。抛开笔墨气质不谈,仅从题材选择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见出他和纯粹的文人画家之间的区别。他的书法楷、行、篆三体兼备。其楷书早年从金农入手,波挑之间分明带有较浓的隶意。他的行楷主要是受了吴昌硕的影响。这一点从其中心紧结、拉长主笔、右肩高耸等结体特征便不难见出。而其在用笔上对笔画起讫转折以及带有隶意的波挑等处的夸张处理,仍可以瞥见金农的影子。他的篆书取法《祀三公山碑》《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等一路掺有隶意的破体书,使笔如刀,不避用笔的刚猛直露,亦不恪守中锋的规范。他的篆刻以冲刀为主,单刀直入,不事修饰,沉着痛快。此种刀法倘非以强悍的腕力与细腻的手感作支撑,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我们把此种刀法与其早年做雕花木匠的经历联系起来看的时候,一切便都豁然开朗了。
这是一个抱着“纵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态度去追求艺术理想的老实人。他的笔墨很少有情绪起伏带来的大起大落,也从无逸笔、信笔,也从不因自恃才高而潦草敷衍。这都是他在长年木匠生涯中造就的品质。人们大都津津乐道于他细心体物的严谨,以至于连鸽子尾羽的数目、螃蟹行动时脚爪的状态、蝉附在树枝上头部向上还是向下等看似琐屑的细节问题都要一一落实而后止,却很少考虑到这种严谨细致的从艺态度与其木匠生涯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画家与木匠的职业属性而论,画家求高逸则可,而木匠求高逸则万万不可。再则,木雕也不比大写意。古时虽有“绘塑一体”的说法,但这种造型原则上的相通性毕竟不能抹杀二者在具体实践方式上的本质差别。大写意的笔墨讲究“欲暗不欲明”,而木雕作品却是锱铢必较,长短尺寸非明而晰之不可。他的大写意出以造型的明白法而绝无笔墨的糊涂相。他画蟹,蟹身、蟹螯、蟹足历历分明,绝无苟且,甚至蟹足的勾爪部分都笔笔送到,不似许多画家的潦草从事;他画虾,每一根虾须都认真地写出,每根之间亦绝无勾带牵连。他是以雕花木匠的态度做大写的事业。他的笔墨是那种典型的“榫卯式”结构,一招一式历历分明,绝不含混。艺术家朱振庚曾在徐渭与齐白石之间做过一番比较。他称徐渭的画是“性情画”,而称齐白石的画是“匠人画”。徐渭画螃蟹,一个螃蟹一个样;而齐白石画螃蟹,所有螃蟹的笔墨套路都是一样的。其实不仅是螃蟹,齐白石画任何东西都竭力去寻找一套明晰的套路。白石老人的作品读来总有一股超乎寻常的整饬与严谨,因为他的作品极少即兴的发挥和临时的补凑。他用笔较慢,自称作画用“楷法”。他笔墨中那股重重的梨枣气最终使他与真正的文人笔墨拉开了不小的距离。他自号“木人”“木居士”,不仅是为了表达对早年经历的怀旧之情,同时也和这段特殊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有关。他的书法早年受金农的影响较大,很可能也是被金农“雕版印刷体”楷书透出的那股浓重的梨枣气所吸引。他的木匠习性带给他每画必有稿样可循的作画习惯,同时也使他养成了比较理性的从艺态度。他的很多手稿上都留有反复推敲改涂的痕迹。即使那不过是武者手中的一根弓弦,或是仙人手边的一根拐杖,他也要一改再改,而其改涂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其摆放的方位、走向未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张力效果。如果没有特别的把握,他还会在稿样中不厌其烦地注明哪怕是一根线条、一块墨色的粗细浓淡。如果没有推敲到非常周致的地步,他不会轻易下笔。他不是那种激情型的画家,他的作品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乘兴而作的方式包含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于他而言无疑都是潜在的威胁。他最服膺的三位大写意画家是徐渭、八大、吴昌硕。但从其传世的作品来看,无论取法三家中任何一家的作品,他笔墨中如影随形的那种梨枣气都把原作中率性、潇洒的文人气质冲淡了不少。
他没有吴昌硕的逸气、黄宾虹的高华、潘天寿的奇崛,但却绝不缺乏质朴与真率。他流传的作品很多,却很少有敷衍塞责的作品。他以卖画为生,作品品质就是他衣食的保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绘画于他而言又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为如果仅仅是谋生,他就没有必要在艺术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那么辛苦。画家为着更好的生活而追求高品质的作品是一回事,但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抱着“我法何辞万口骂”的态度不淫不移地实践自己的变法主张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虽拥有高度的写实能力,但他从不滥用这种能力。他以“太似则媚俗”的警语告诫世人,这说明他对这种能力极易造成的负面影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人们总喜欢津津乐道于他的工笔草虫功夫,其实白石老人绘画的妙处又岂仅在区区草虫呢!他在绘画技巧方面绝不炫奇,也从不故作高深。一般文人画家论画都不免形上形下一番,而他的论画语从来都是极其平实的话语,以至于当李可染问及执笔的要领时,他唯以“不要让笔掉下来”的朴素语言来应对。再如同样是对于“似与不似”这一美学命题的发挥,石涛说:“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他则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同样的命题,石涛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且表现得很有涵养;而齐白石在申明自己立场的同时,却不免有自我托大的嫌疑,因为他把画得“太似”与画得“不似”的人都列入了批判的行列。
他是那种雅俗共赏的画家。但和任伯年、王雪涛等画家以过硬的写生功底贴近生活的美学取向不同的是,他的“俗”是结合了民间造型的结果。不厌其烦的细节堆砌和整体造型的高度意象是民间艺术的特色,这种由细节之“似”与整体之“不似”的强烈反差所构成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张力结构也正是白石老人成熟期的作品与其他画家作品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白石老人熟谙工写的辩证法。他所涉足的宽广的造型领域使他可以在工与粗的两极之间优有余裕。他画荷叶只几笔便写出大的形体,却用工整到近乎板刻的线条去勾勒叶筋。至于其画荷花花头勾筋的办法更为他之前的大写意家所未曾有。他画梅干无论粗细均用书法笔法一笔写出,却极其认真地分别出梅花正侧反转的形状,并细细剔出每一朵花的花蕊。他画紫藤藤枝离披,如篆如籀,花叶的点厾与勾画则采取如装饰图案般整齐的对称结构,甚至连每瓣藤花的花柄、花托都不肯轻易放过。他画葡萄粗枝大叶,但却醉心于那些缠绕在枝叶果实之间的细细的毛须。他画玫瑰花只几笔便涂出花头,却用朱砂细心地剔出枝干上的尖刺。自然,他也并不反感在画面中解决玫瑰花叶那锯齿状叶缘如何表现这类看似无关紧要的课题……
在变形处理方面,齐白石同样受到了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民间艺术主要是为着传达公共经验的需要,因此其相对简约的形式特征与相对恒定的程式化处理实在是为着认读与传达的方便,故它的变形处理大都体现为摆脱了参照对象自然尺寸之后极富装饰意味的符号化、半符号化状态。如果说吴昌硕的变形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原生感受上升到图式层面的自觉化用,那么齐白石的变形则和他将自己熟稔的民间造型原则移用、嫁接于文人笔墨的变法策略有关。民间造型的特点有二:一是形象的极度夸张,二是浓厚的装饰意味。齐白石动辄夸大物象尺寸和分量的做法乍看与吴昌硕有几分相像。但吴昌硕的夸张是有意无意间放大自身造型感受的结果;齐白石的夸张处理则和他将民间艺术的造型理念贯彻于其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识有关,如他笔下硕大无朋的寿桃形象便绝非文人画家所可梦见。民间艺术在气氛上求其热烈,在造型上求其饱满。究其根本,乃在于造型的饱满、丰硕是生命力度的象征。而齐白石这种夸大对象尺寸、分量的做法正源于民间艺术的这一造型原则。
再如对称与重复这两种构成方式的运用。白石老人笔下的叶片组织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画的牡丹、菊花花头的造型和花叶的组织,熟悉民间艺术的观者一望便知是源于传统木雕的惯用程式。他的叶片组织几乎是主动放弃了由透视翻转带来的丰富视觉形态,而是做足了归拢、简化的功夫,使之看起来更像是单位元素的不断重复,同时仅用色彩、浓淡、勾筋的变化来提示其必须具有的层次感。他画牡丹,如果是几朵花头同时出现,他甚至不惮将这些花头画成大致相同的模样。这显然是绘画中比较忌讳的方式,但在民间艺术中却是习见的手法。他画菊花花头刻意摒弃了花瓣的自然形态,排列规整,一如装饰图案。这种处理和我们惯见的菊花花头画法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白石老人不仅善于利用程式,也同样善于创造程式。如他画松树时,树干的画法并不采用传统的鳞片皴,而是以类似于解索皴的粗笔勾画。这种方式是前人所没有的。再如他笔下的石头完全继承了吴昌硕的顽石、丑石美学,却较吴氏更为简练、抽象。这些石头用阔大的笔触写出,几乎不费皴擦染点之功。这种石法同样是属于他自己的方式。白石老人高度重视自身的生活感受,并绝不因片面强调程式的作用而迁就生活感受的真实。他画作的造型乍看上去有着极强的程式化特征,但只要用心体味,就不难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他画葡萄果实用圈勾法,利用色彩的沁渗体现其富含汁液的通透效果;画枇杷叶子用粗重的排状叶筋表现其肥厚的质感。这些都是他善于利用程式、创造程式的极佳范例。
白石老人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几个时期。他的造型能力非常全面,这和他一生经历的几个时期有很大的关系。他早年学做雕花木匠的这段经历使他深入了解了民间造型的艺术特点。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也临摹过《芥子园画谱》,但主要是为了将其应用于木雕,所以还难说文人画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他在学文人画之前还画过祖宗像。虽然祖宗像在古代被视为匠人画之流,但它对形似的功夫要求很高,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齐白石的造型能力。他学画美人画有类似于改琦的小写意画风,学扬州八怪、徐渭、八大、吴昌硕的东西则是大写意,而其草虫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工笔,尽管这工笔是画在生纸上的。他变法之前的作品面貌既多且杂,造型方式也不固定。这一时期他大都是在别人的图式里面讨生活,而他的衰年变法则是将早年木匠生涯中熟习的民间造型和主要是从吴昌硕那里得到的笔墨方式融合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在经历了正、反、合的曲折历程之后,他以吴昌硕为触点,重新点燃了在他骨子里面沉睡着的民间情愫,实现了个性化的创造,所以变法之后的这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他的回归期,而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在他的花鸟、山水、人物画当中都体现得相当明显。白石老人的笔墨从吴昌硕那里获益最多。和吴昌硕相比,他不如吴昌硕的率意,却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洗练;他没有吴昌硕丰富的笔墨层次,却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清透;他缺少吴昌硕的野逸之趣,却也因此而显得更加稳健。人们津津乐道于吴昌硕对齐白石的影响,却很少看到齐白石善于化用的功夫。齐白石在取法吴昌硕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的造诣。我们从胡佩衡的《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一书中不难了解齐白石学习吴昌硕的详细情况:他常常是把吴的作品张挂起来仔细地揣摩,然后凭印象去画,画成之后再行比对,所以他临摹吴昌硕的东西主要是意临。我们之所以很难见到白石老人学吴昌硕学得很像的作品,也和他的这一取法方式有关。他是边学习边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昌硕于他而言更像是一个契机、一束点燃他全部艺术能量的火花。他借鉴了吴昌硕,又透过了吴昌硕——他是一位真正的善学者。
相关文章
- 师从任颐,和吴昌硕亦师亦友,蒋介石赞:清标亮节2017-10-27
- 知道每天电脑输入的行楷字体是谁写的吗?2017-08-10
- 石涛致八大山人书: 哥们来张画儿2017-08-08
- 徐悲鸿画猪:气韵生动,憨态可掬2017-07-31
- 一树梅花一年翁2017-07-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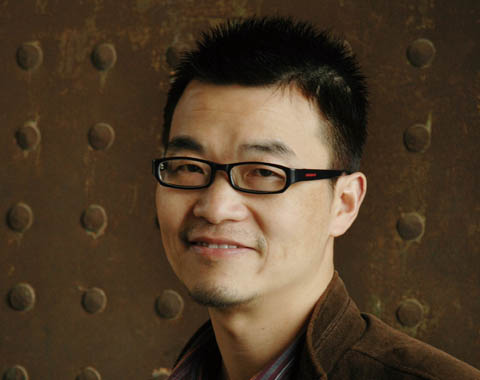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黄文泉 诗意的行走
以文泉于楷书勤苦之根基,其行草研习可谓平川走马,纵
-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 谦和悟道 执着追求
张华的篆书与篆刻都是小写意风格,他准确地把握每个字
-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刘子安 又于淳醨见古今
书学通心学,阳明讲“心即是理”,伯安又言“心外无物
- 陈鹏酒后戏作《将进酒》(上)
- 10月13日夜,老鹏做客择一堂,酒后戏作草书《将进酒》8条屏,有幸得孙辉兄拉纸,王伟平兄、杨圣山兄拍摄。...[查看全文]